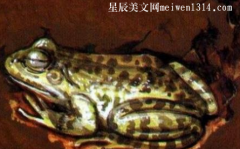许我一树春暖花开
2017-06-07 09:04:06 作者:赵安刚
我,躲在医院楼道的出口处,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任由泪水狂流。烟头在指尖颤颤巍巍,它也喘着长长的粗气,不停地在黒暗的夜色里抖动,跳跃。暗红的烟头,在空气中撕裂出一道一道的弧线,莫名变换出一阵阵青烟袅袅而去。它努力地挣扎,它想逃离,逃离这个使人窒息的黒幕。
刚才的情景,使我的肉体和神经一起扭曲,挛动。病床上的娘,弯着腰,头拱着床,扭曲着干瘪的躯体。额头上的汗水,不时地从她凌乱的头发里渗出。多日的病痛,她已形容蒿蓬。她,已经没有力气大声shenyin。只有干裂了的嘴角边的颤动,和眼眶里无声的泪水,还有降不下来滚烫的体温。我真切地感受到她正在承受着炼狱般的苦痛!

这是谁在大声奔呼?这么熟悉的声音……是娘在叫吗?是!一定是!坐在床边的我,恍恍惚惚之中被这激厉的声音点燃,炸开,幼时的那些点点滴滴刹时涌上心头……
娘,是从冀南平原来到这个大山中的,相夫教子。小的时候,我一直喊“娘”这个称呼。同龄人常常学我,笑我。再大些后,称呼自然而然的就融汇到大山里了。然而,“娘”这个词汇永远融合到我的血脉之中。记事起,母亲shenti一直不好,她有严重的气管炎。一天到晚总是能听到不断的咳嗽声。她xing子刚强,常与父亲吵嘴逗嘴。父亲本xing为人善良谦恭,体贴母亲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总是让着她。他为了我们能吃上饱饭,每日在生产队里辛勤劳作,晚上又在队上马棚帮护喂养牲口,为了多挣些工分。母亲在家勤俭持家,每天天色不明就去临近的工厂,淘拾工厂锅炉烧煤遗弃的煤核,回来以备家用烧水做饭。白天则与他们一起下地干活。他们为家辛勤操劳,尽心奔波忙碌。
记得很小时,也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奇怪的是,没有记忆中的闪闪星光,没有皓月当空。三更时分,我忽然得病发起了高烧。昏昏沉沉中的我,被母亲匆匆背起,她披襟散发,赤着一只脚,步履慌张地去卫生院找医生。那个黑夜艰难漫长,路上没有一丝亮光。她大声拍打着卫生院的大门,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医生……医生……快…快开门…
当医生打开铁门的那一刻,她即刻瘫软在地,不停的喘着,大声的咳嗽。吓得医生赶紧把她安顿在卫生院的病床上。
时光流逝,岁月无情!如今,我们兄弟几个早已成家立业,儿女缠膝。父亲却离我们远去经年,母亲也年衰苍老,病魔缠身。父亲在世时,常常对我念叨:“你娘养活你们几个不容易,她背井离乡,远离故土,来到咱们这里。你们弟兄几个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你娘”。
渐渐的,我们也都生为人父,体会到父亲对母亲的那份深情。也深深地理会到了父母对儿女的那一片血脉之情。天冷,怕孩子冻着,热了,怕孩子热。儿女远行期盼孩子平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提笔到此……思来,不由得我泪眼迷离。
轻轻拉起她瘦弱的手,干瘪的胳膊上青筋密布,看着她失神无助的眼眼,我知道,这个叫“娘”的风烛老人,也许……不久的将来将与我们缘份散尽,独步远行!(星辰美文网www.meiwen1314.com)
此时此刻,耳边却不由得响起了一首痛彻肝肠的二胡小调;“桃花儿不再红,杏花儿不再白,松木板,柏木档,一把黄土埋了娘………
我遥祈苍天;请许我一树的春暖花开吧!让娘再多看一眼,一地的桃李芬芳,满院的瓜果飘香吧……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