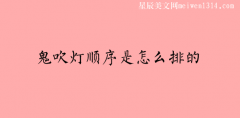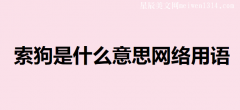当前位置: > 原创美文 > > 正文
孵蛋的母亲
2019-01-24 13:56:20 作者:孔令燕
金黄的银杏叶悠悠地落下,轻盈地投入大地母亲的怀抱。在这牵动情思的深秋,不禁想起我那会孵蛋的老母亲。
童年的冬天,难熬的季节。天寒地冻,干冷蚀骨。放晚学归来,我推开院门,锐声呼喊:“妈!”因寒冷,声音颤抖起来,打着旋儿。笔直的烟囱,缕缕青烟袅袅飞天。母亲照例笑嘻嘻地立在厨房门口,我欢呼雀跃,两只冻僵的小手如同找到了火炉,兴奋地钻入母亲的怀中。
“来,喝杯热水。”
双手贪恋母亲的体温,嘴里吞咽着茶水,心儿也跟着解冻。
又是一个寒天。放学后的我,闷闷地钻进西屋。虽双手冻得发红,也没找那只“火炉”。母亲悄悄地踅进屋来,柔声问:“怎么了?”我兔子般的红眼睛眨巴着,不吭声。母亲轻轻地将我的双手揣入她的怀中,再问:“怎么了?”“老师打我了!”我的泪水如决堤的洪水,“我只是说一个男生帽子像日本鬼子,老师上来就甩我一巴掌!”揭开伤疤的痛苦让人不堪。沉寂,心痛的沉寂。终于,母亲将我揽入怀中,轻声开导:“一巴掌算什么?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冤屈死多少人啊。邓小平还三上三下呢,受了多少磨难,他还不是国家领导吗……”母亲的话我不完全懂,但她的怀抱抚慰了我受伤的小心灵。

后来,为了贴补家用,也为了我们姊妹仨的学费,春寒料峭的清晨,瘦小的母亲冒着寒气,顶着冷风,挎着一篮新鲜蔬菜去集市上卖。从集市上回来,母亲急匆匆跑进厨房,来到灶台后的旮旯里。一层厚厚的稻草散发出淡淡的草香,一只老鹅紧紧地伏在上面,肚子底下藏着十颗鹅蛋。当时一对小鹅五元钱,这十颗鹅蛋可是我们学费的重要来源呢。母亲高兴地抚摸老鹅的头,默算着老鹅孵蛋的日子,闪亮的黑眼睛里充满期待。
日子在母亲爱抚的手中悄然流逝,一只只小鹅破壳而出,本就羼弱的老鹅更加消瘦,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母亲看了很心疼:“你瘦了,脸都瘦扁了!”老鹅一摇三晃地踱进厨房,想尽母亲的最后一份力——干草上还有两只孤零零的鹅蛋。
瘦小的母亲看着憔悴不堪的老鹅,叹了口气,又去院中忙活了。待再回到厨房时,母亲一声大呼“不好”,可怜的老鹅歪歪斜斜地躺着,腹部下露出两只温暖的鹅蛋。爱到无力,无能为力。
望着那两只蛋,母亲眉头紧锁,忽然灵光一闪,竟找来一条长长的绿围巾,紧紧扎在腰间,继而解开棉袄,把两只鹅蛋小心翼翼地放进去。就这样,母亲温暖的怀抱,变成了蛋蛋们温馨的港湾。母亲又慢慢俯身,轻轻地将老鹅抱到庭院的阳光下,给它吃最鲜嫩的菜叶。那天,母亲做什么事都放慢了节奏,仿佛怕冲撞了神明似的。终于捱到了晚上,疲惫的母亲坐在窄窄的床头,紧了紧腰间的围巾,将坚硬似铁的棉被高高地拥在周围。此时,母亲的怀抱是最美好的温床,蛋蛋们疯狂地生长。灯光如豆,困乏的母亲强打精神纳起了鞋底。戳长针、压顶针、拔鞋拔、拉麻线,原本行云流水的连贯,此时变成了按部就班的慢镜头。母亲似乎感受到了鹅宝宝均匀的喘息,听到了嫩嘴啄蛋壳的“叮叮”声,越发小心翼翼地重复着每一个动作……
第二天清晨,“嘎嘎”,“嘎嘎”,稚嫩的声音从母亲房间里传出,两只毛绒绒的小黑鹅在她双脚间来回穿梭。瘦弱的母亲双眼布满血丝,眉宇间却是掩饰不住的喜悦和自豪,窄窄的床头摆放着一只已经纳好的鞋底。
庭院中春阳融融,羼弱的老鹅缓步走着,大扁嘴时不时地碰碰那两只可爱的小黑鹅,眼光中充满怜爱。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到了开学的时候,十只小鹅苗一对对相继卖出,母亲的嘴唇抿得很紧,黑亮的眼睛里满是不舍。那一学期我们的学费交得很干脆。
母亲温暖的怀抱不仅孕育出鲜活的生命,更融化了我们成长路上的坚冰,帮助我们由“农门”跳进“龙门”。
母亲,您就是一只羼弱的老鹅,我们都是您倾尽心血孵化的蛋啊!
母亲唯一的念想是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们……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