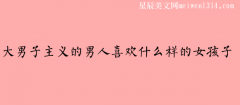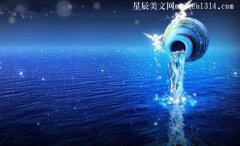《小留香馆日记》读后感
2017-04-18 00:30:27 作者:星辰
去年读了《京剧谈往录》中荀慧生晚年的秘书、也是政府派到荀剧团的干部张胤德的一篇文章,知道荀慧生大半生坚持记日记,几十年如一日,这在梨园界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荀慧生从成名后的20世纪20年代开始坚持写日记,一直到狂飙袭来的1966年为止,总共累积了44本,用他自己的书斋名命名为《小留香馆日记》。荀慧生幼年即投师学艺,文化水平不高,因此他的这些日记很少是自己写的,大都经他口述,由身边的人替他执笔,如早年的陈墨香、晚年的张胤德等。文化大革命中荀慧生被批斗、抄家,他本人也于1968年底溘然长逝。所幸浩劫过后荀慧生的日记竟完好无缺地保留下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文革后俞振飞到北京,在荀慧生的遗孀张伟君那里还读到了这些日记的手稿。但难以预料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在后来荀家分家的时候这些日记被子孙们瓜分的七零八落,散佚大半。如今我拿到手里的这本《小留香馆日记》仅收录了1926、1928-1934、1942-1944年的日记和1957、1959年的部分日记篇章。这已经不是荀慧生44本日记的全貌,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认为书名定为《小留香馆日记残本》也许更合适。我本以为荀慧生大师的这本日记是艺事日记,记录的都是排戏、演戏的事。然而当我读到这本书时发现并非如此。日记中所记多为生活琐事,对于艺术反而涉及很少,即便提到演戏的事也往往是一笔带过。即便这样,日记仍然引人入胜,因为内容十分真实,全面再现了民国时期一个享誉全国的当红名角的日常生活。真实是日记的生命,否则就成了文学创作。荀慧生的日记自始至终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从文字到吐露出来的情感,莫不如此。本来荀慧生写这本日记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自己生命中的酸甜苦辣都记录下来,就像张胤德说的“他要倾吐他的感情,于是他就要记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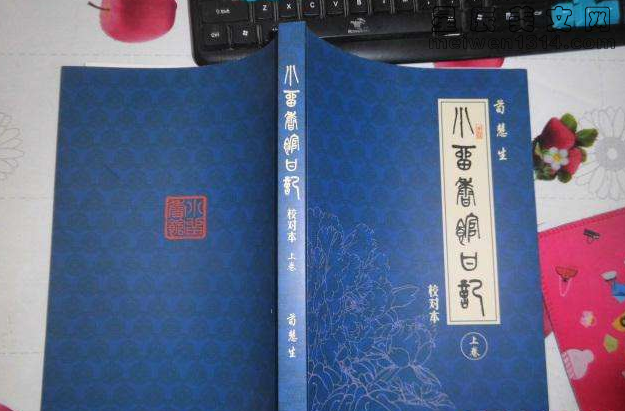
荀慧生自幼家境贫寒,很小的时候他们兄弟就被父亲卖给一个梆子艺人庞启发学艺。庞待荀慧生如同囚奴,终日打骂。一次给荀慧生看功的师傅竟不慎把他的腰给折断了,而生命力顽强的荀慧生居然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又康复了。后来荀慧生改学京剧,并和尚小云、赵桐珊等同在正乐科班学戏,出科后艺名“白牡丹”,终于一炮而红。荀慧生的成功之路异常艰辛,前半生的路途十分曲折。在1928年11月1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此剧(指《钗头凤》)极为哀艳,自顾身世多与剧中人相合,每演之未尝不泪盈盈下也。”1941年9月6日他又写道:“余幼时被父母兄长压迫,胡搅家庭;不想内子亦是如此,命里注定。”唐鲁孙有一篇文章叫《故都梨园三大名妈》,与此相对的还有“四大名爹”。旧时梨园行里这“四大名爹”包括李少春的父亲李桂春、李万春的父亲李永利和谭富英的父亲谭小培,唯一一位外行就是荀慧生的父亲荀凤鸣。荀凤鸣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养活不了孩子就卖给别人。但等荀慧生唱红了的时候他可是大显威风。他对荀慧生逼得很紧,虽然按时给他送钱也不能令他满意,经常上门要钱,还逼荀慧生出外走码头挣钱,甚至于在有荀慧生戏码的堂会上都敢跟人家大吵大闹。荀慧生对自己的父亲很无奈,可以看出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感情,时不时地在日记里发几句牢sao抱怨一下老头子。荀慧生的前半辈子缺少家庭的爱、父母的爱,这对他的xing格可能有着较深的影响。
旧时唱戏的不抽鸦片烟的可谓寥寥。荀慧生也沉湎于这一嗜好并深受其害。他在1929年10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吸烟三年,今矢忌断,体颇不适,实自取烦恼也。”他很早就开始抽鸦片,也很早就认识到了鸦片烟的危害。荀慧生不止一次地在日记中立誓要戒除毒瘾,他也真的不止一次地尝试戒烟,甚至为此数次住进医院。但荀慧生从来没有戒烟成功过,一则他的毒瘾很深;二则梨园行里人人有阿芙蓉癖,他的妻子吴春生也吸鸦片,这种环境在一定程度了也影响了他的戒烟效果;再者荀慧生不仅要担负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而且他的班社中其他演员的生计也全都指望他,因此他的演出压力是相当大的,同时他还要应付各种繁忙的应酬活动,当他精力不足时就不得不借助于鸦片的效力。荀慧生日记中所记的几次上海演出,无不是依靠鸦片支撑的。长期吸食毒品严重损害了他的shenti,但他没有办法,他要上台、他要演戏、他要赚钱,他只得依靠鸦片来勉强支持,他甚至因此而几次差点丢掉xing命!一般人看到的只是舞台上光彩照人的大牌红角荀慧生和他塑造的那一系列鲜活生动的好角色,如果不是他的日记,谁又能知道他在背后遭受的这些痛苦呢?
荀慧生是大角,是“四大名旦”中唯一的花旦。他一辈子挣了多少钱可能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当年的演出收入,比如1941年4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张伯铭送来一日堂会《辛安驿》戏份洋四千元。”一出堂会戏的戏份高达四千元,他与梅、程、尚四人合灌《四五花洞》唱片的报酬更是高达4500元。这个收入实在是惊人的。荀慧生喜欢竹戏,也就是打麻将。他曾在上海演出期间一夜输了一万多,平日里打牌输掉几百或几千元更是不足为奇。有钱的荀慧生不惜花费重金营造住宅,还广购房产,后来甚至开办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留香大饭店”。当然这些事情也一度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特别是这间饭店。荀慧生在日据时期开设这么大的买卖本来就是一招错棋,何况他之前又没有任何经商经验,结果自己被弄的心身俱疲、钱财费尽。他在1943年2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日来为饭店账目不清、琐事繁杂,日夜寝食不安,苦不可言……”他开办留香饭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花钱找罪受”。本来俨然巨富的一代红伶因为不惜举债开办饭店而搞得自己捉襟见肘,开始拆东补西了。为了偿还债务,荀慧生甚至连自己居住的宅子都卖掉了。他在1943年7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年粮食困苦艰难,都城贫人饿死大半,可怜!今夜余家缺粮……所谓等米下锅,四十年来未经过此等苦境”,7月29日又写道:“每日为杂粮筹措不息,逢人必托购,不顾价钱高低。”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抗战时期时局艰难,但荀慧生这样的人物都落到“等米下锅”的地步实在与他商业上的失败是大有关系的。
荀慧生作为伶人,交游很广。上海的“三大亨”、虞洽卿、顾竹轩乃至张宗昌都是他的好朋友。旧时北京城里有“四大名医”,即萧龙友、汪逢春、孔伯华、施今墨四位。(星辰美文网wwW.mEIwen1314.CoM)其中荀慧生与汪逢春相交甚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荀家的人但凡有什么病痛灾难都请汪逢春来加以调治,因此从荀的日记中我们得以一窥这位一代名医的侧影。1933年5月20日汪逢春来看望荀慧生,对他说:“情愿作亡国奴,不愿作民国人”,还说:“日本早来,小民之幸也!”当然汪逢春的话是比较偏激的,但是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老百姓对国民政府的极度不满。像这样受到老百姓深刻仇恨的政府是绝对不会长久的。荀慧生为人有其讲义气的一面,比如他曾扶持了困境中的赵桐珊。荀慧生当年到天津演戏时遇到曾同科学艺的赵桐珊流落天津,于是他将赵带回北京并留在自己班中演戏。等赵桐珊时来运转之后却同时在荀慧生和高庆奎的班社中充当硬配并乱涨包银。气愤之余的荀慧生在1932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写了一首骂赵桐珊的打油诗:“后悔当初一念差,不该天津救济他。这样人心实可怕,交他不如养鸡鸭。伊今买房架子大,东骗西诈把钱抓。随余京津把南下,这才有钱发了家。小人乍富实可怕,从今以后防备他。”还有1930年5月25日诸名伶在第一舞台演义务戏,其中《长坂坡》一剧原本定的是程砚秋的糜夫人,但程却去另一个地方唱堂会了,惹得“官场大为不悦”。在这种情况下,荀慧生“自愿代演,其气始平”。这种江湖救急的行为确实够义气,尤其是在梨园行,又都是唱旦角的。荀慧生的这种做法实在堪为后辈楷模、梨园典范!“四大名旦”当年竞排新戏以招徕观众。要排新戏首先得有好剧本,于是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编剧,比如齐如山之于梅兰芳;罗瘿公、金仲荪之于程砚秋;李寿民之于尚小云,荀慧生的编剧就是陈墨香。荀慧生与陈墨香相交既久,陈为其编的戏有《钗头凤》、《红楼二尤》、《荀灌娘》、《美人一丈青》、《孔雀东南飞》、《鱼藻宫》等共计50余出。陈墨香还和荀慧生合作在传统的“起解”、“会审”、“监会”、“团圆”等折的基础上编成了全部的《玉堂春》。陈墨香对荀派艺术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但后来他们二人之间生了嫌隙,终致分道扬镳。陈墨香曾为程砚秋写了一个剧本,荀慧生知道后大为不爽,他在1931年1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窃忆予与伊(指陈墨香)相处已十余年矣,自问对伊尚好,何以近来伊老表示不满?”在1933年4月3日的日记中又骂陈墨香“得新忘旧,可称势利小人,令人伤心”。1942年5月1日陈墨香去世,荀慧生送了四元赙仪。当时的报纸上骂他是“四元名旦”,各种攻击纷至沓来。记者们还把荀慧生和程砚秋相比,说程砚秋在罗瘿公生病期间和去世后承担了一切费用,如何仁义;而荀慧生如何不讲仁义。不管别人怎么说,荀慧生这么做总有他的理由,他在1942年5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但同墨香感情在世时已伤,早成恶感”。最后在众人的解劝下荀慧生还是为陈墨香演了一场戏,所得的413元2角悉数送给了陈墨香家属。
《小留香馆日记》中还记载了荀慧生对于当时名人的许多评论,值得玩味。1933年5月4日程砚秋去看望荀慧生,二人品评梨园人物,说梅兰芳“堂会戏码时常摆布人,阴险诡计,实在可恶”!据日记中所说,“二人同病相怜,畅谈甚久”。1933年7月13日程砚秋自欧洲游历回来后首次在中和园演《贺后骂殿》。这出戏是一出骨子老戏。据说过去只有陈德霖敢演,因为戏太瘟。程砚秋在王瑶卿的帮助下对这出戏的大段唱腔进行了改革,使得这出戏大受欢迎,从此也成为程砚秋的拿手剧目之一。荀慧生在这一天的日记里骂程砚秋:“戏票价甚昂,两元之多,借外国新回,身价增高,敲本国人竹杠也!戏价如此贵法在北平为破天荒也!”赵桐珊、筱翠花、朱琴心、徐碧云等都是旦行中地位仅次于“四大名旦”的名旦,其中芙蓉草赵桐珊因很会演戏而被多位名角倚为左右手。荀慧生在1930年2月22日的日记里对其评价道:“(《鱼藻宫》)桐珊之吕后表演真切,泼辣凶狠,入骨三分。台下观众竟有将蔗滓、橘皮纷掷其身,亦可见此剧之受人欢迎”。1941年8月13日荀慧生在长安戏院看了童芷苓的《红楼二尤》,说:“模仿余不过皮毛而已,实在对于戏情无有揣摩”。同年12月20日他又在广德楼看另一位学荀派的吴素秋演《红娘》,说:“模仿余相像,稍觉迟笨。”童芷苓和吴素秋这两位荀派传人当年曾以“劈纺戏”红遍全国,我看过她们晚年留下的几出戏的录像,认为这二位都是极会演戏的好角。1944年3月23日荀慧生在上海黄金大戏院看童芷苓演出的《大劈棺》和《纺棉花》两出戏,说:“《劈棺》失却戏意,信口开河,大说上海话之流言;《纺棉花》尤甚,学四大名旦之短处变本加厉,在台上时与台下人搭话,任意胡闹,时装打扮,略微遮盖肌肉而已,几成卖笑生涯之变相。”这一段评论可以视作是关于“劈纺戏”的宝贵资料。1942年4月8日看了话剧《雷雨》以后荀慧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种种剧情“结果均明了:死、走、逃、亡。”
这部《小留香馆日记》中还记了一些事,读来令人捧腹。1930年6月2日是尚小云妻子去世送库。所谓“送库”是指给亡人祈建的道场圆满时,由丧属捧着给佛的黄表到指定的地点去焚化纸活冥器。老同学的妻子去世了,荀慧生当然得去送一程,但他因“天热、身累”就想提前走掉,但“为小云监视未果”。读到这一段时我觉得荀、尚二位大师实在可爱:荀大师去给同学妻子悼亡,去了意思一下就想溜之乎也;尚大师心说给我老婆送库,你们一个都不能少,挨个盯着他们。还有1932年3月3日晚上荀慧生另一重要配角、名丑马富禄在荀家打麻将,他的妻子这时候找上门来了,荀慧生说:“富禄吓得面无人色,急偕同伊夫人回寓。诸友莫不捧腹。”原来马富禄不光是名丑,还是个惧内的名丑呢。
相关推荐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