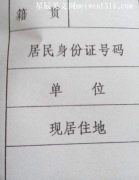当前位置: > 情感日志 > > 正文
老家
2017-06-08 13:47:17 作者:王苏兰
我也想家了,是我住到二十几岁才从那里嫁出去的老院。
哥家没人,就只有母亲在老家了。
一种熟悉又久违的感觉,就像是从前从远处归来却不见父母,幸福、热切,又委屈。

地是刚扫过的,上屋的门虚掩着,木门槛和门墩儿还是老样子,只是旧了。门前的地上不再有鸡粪痕迹,檐下、窗台上的灰白色的鸽粪倒是不减。屋顶上一群灰色鸽子走来走去,咕咕的叫声给老院平添了几分生机。看到这兴盛不衰的鸽群,想起来多年前的事:头发花白的老父亲站在梯子的尽头,不顾母亲的恼怒和我们的惊呼,在屋檐下给野鸽子订了一排小窝,从那时候起我们家就有永远清理不完的鸽粪和鸽子羽毛,偶尔还有野小子们探头探脑的觊觎。
东上屋一直是我们姐妹的“闺房”,直到两个姐姐出嫁,哥哥搬出去另建家园,我才从这里搬到西厢房。屋子西半部原来有一顶芦苇系的浮棚,下面是我们姐妹的床。那时候每到晚上,三姐妹挤在一张床上,浮棚下吊一盏昏暗的灯泡,大姐在做针线,二姐在另一头跟着学,我就坐在中间,把书本按在腿上写字。我和二姐老是蹬来推去的争执不停,因为小,大姐回护我,我总能告赢二姐。清贫的日子,现在回味却全是幸福温暖。
院子里有动静,母亲回来了。看见我从屋里出来,母亲明显吃了一惊,不过马上就笑了:俺小闺女回来了… …一边递过来几根木棍,要给豆角搭架子。(星辰美文网www.meiwen1314.com)
菜就种在原来西厢房的位置上,那里是我长大后的“闺房”,如今房子塌了,留一截短墙参差立在那儿,墙上犹有我留下的痕迹。那里种的菜倒是生机勃勃,可是我还是伤感起来。我的小屋啊,曾经有过我多少年少青春的梦在这里弥漫,承载过我多少的快乐感伤,那是我永远不会忘怀的地方。
北墙曾是我贴画的地方,一张水墨荷花是我的最爱,就那样画在一张宣纸上,不曾装裱,质朴而灵秀。还挂着我自己做的拼装画,伶伶一枝墨绿的花。窗下是哥哥亲手做的桌子,立着我寥寥无几心爱的书。书间cha的一枝绢做的黄玫瑰,几可乱真。药架即是隔墙,将我的闺房变得小而温馨。我喜欢开窗让阳光进来,窗外的石榴树枝桠伸手可及,花和花苞红的耀眼,那叶子碧绿的泛着油光,我有时会看痴。那时候听到一首歌会流泪,会睁着眼睛在黑暗中躺到午夜,会在日记中写许许多多的心情和诗,长长短短的句子,多是不知名的忧伤… …青春,就这样远去了,而见证我青春的小屋,也不复存在了… …
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伤感,转身去了正屋。
坍塌了的是我的闺房,隔壁小弟的屋子还在,木床上的苇席还在,有薄薄一层灰尘覆盖。弟弟少年离家,不知道对他的屋子还会有多少记忆。看见那个墙上的cha座,想起弟弟四五岁时曾经将小指头伸进去,触了电的他惊恐万状,再不愿接近那堵墙。而今,在电路方面,他可是高手一个了。
正屋是一家人的活动中心,小时候没有感觉,长大后总觉得棚低了,压抑。套间是父母的住室,几十年前的旧铁床还在原地,小窗上的玻璃也还明净。墙上挂东西的钉子都还在,小弟写在上面的粉笔字也依稀可见。东西邻居的房子都是新盖不久,我们的老房子就显得低多了,因为房后排水不利,后墙已经湿到二三尺高。西邻建房时损坏的房脊,留着一道宽宽的缝,我能看见外面的天。老房子真是住不得了。老迈的父母搬离这里时的无奈和不舍,我能够深深体会到。这是他们的王国,每一片砖石都是他们的血汗,每一株草木都是他们的爱怜,灰瓦土墙,都留有他们的温度。孩子们都长大了,飞走了,只有这个院落不会变,晨辉日暮,寒来暑往,陪他们慢慢变老。它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最踏实的所在,是他们的主心骨,离开它,何尝不是切肤之痛?
这里曾经是“家”,如今人去屋空,只能称之为老院了。我知道在将来的某一天,它终究也会被夷为平地,但我祈祷那一天无限期的推延,不会被父母看到,最好也不被我们兄弟姐妹看到… …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