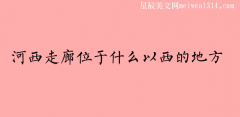那一年的雨天
2019-03-15 21:38:11 作者:张光中
眼前淅淅沥沥的连绵雨天,把我的思绪带到了从前,那个脑海里抹不去的雨天……它是镌刻于心,让我难以忘怀。
我的故乡石咀会,是个不足三百人的小村庄,村子交通便利,但最大的问题是缺水,祖祖辈辈因为水的问题而无奈和揪心。全村唯一的水源就是离村子一里多地以外的南山上,我们叫井道坡。井在半山腰,村里人担一次水要跨过一道河,再爬几百米的山道才能到达。这种山道多是土路,没人整修,非常难走。
井里有一股空山水,空山水和泉水的区别就是,泉水自成水系,水量一般很大,而空山水全凭山里面的水慢慢渗透下来,汇聚在一起,水流量很小,日流量超不过一方。由于水量小,打水的人多,水井里永远不会存过多的水,水深不及一桶高。于是人们在担水桶旁都挂一个小水葫芦,村民们都叫他圪捞,这种圪捞芦呈扁平状态,尖底,系上绳索放到到井里后自动放平便于进水,一担水要这么起起落落十来次才会灌满。
当然这很难满足全村人畜饮水需要,于是一些条件好的家庭便用手推平车改装拉水车到外村拉水吃。
我家条件不好,人口多,收入少,根本买不起水车,于是只能靠在井道坡担水吃。我父亲那时候在回龙供销社任采购员,常年不着家,我大哥到外面找工作,二哥在外地学徒,于是全家的吃水重任就落在了我的头上。十三岁的我自动成为了家庭担水员。
于是,每天的早晨,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身高不到一米五,体重不达一百斤,要挑着一担装水五六十斤的水桶,行走在崎岖的小路上,走一步都摇摇晃晃,颤巍巍的。
也是一年的夏季,也是连绵的雨天,家里水缸已经快见底了,我咬咬牙,决定冒雨上山挑水。一般雨天的时候,由于人们很少出去担水,井里应该能够积攒不少水。我这么想着,于是,收拾桶担出门。
连续几天的雨,河里也起水了,但还可以踏着石头过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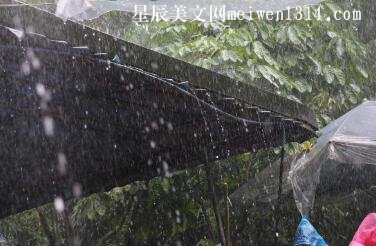
来到井边,哈,水还真的不少,轻轻松松灌满水桶准备下山。这时候,问题来了,山路经过雨水浸润变成了泥路,上山是空桶,不觉得太难,可下山是实桶,平常走都得小心,何况雨天。
担起水桶我万分小心,尽量走路边长草的地方。每走一步都要试探试探脚底下是否虚实。生怕发生变故,可怕啥来啥,事情还是发生了,走到一半路程,突然脚下一滑,我四仰八叉结结实实的摔倒在泥路上,浑身上下沾满了泥巴。担子别在一边,两只水桶也顺着山坡咕噜噜滚下山底。
我的情绪终于奔溃了,这么多年的心酸一下子涌上心头。我索性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在这空无一人的山坡上,尽情的哭。雨水、泪水交织在一起。我恨,为什么我生在这个地方?我恨,为什么我们村这么缺水?我恨,为什么我家连一个水车也买不起而必须挑水。
没人来安慰我,也没人来帮助我。想想家里人还在等水吃,我默默的摸一把眼泪,起身走到山底,拾起滚落的空水桶,毅然返回水井重新灌水,然后再重新小心翼翼的下山。
相关推荐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