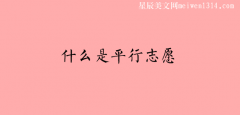看麦
2019-08-28 02:06:49 作者:丰年雪

“算黄算割,算黄算割。。。。。。”,每年到了家乡的麦收季节,就有种神奇的鸟儿,把发音清晰、高亢嘹亮的叫声,响彻在金黄的麦浪上空,响彻在庄稼人的心头;更为神奇的是,只要麦子收割完毕上了晒场,这种鸟一夜之间就会销声匿迹、无影无踪了。
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碌起来,为收麦做着各种准备。看吧,男人们修理拉车、打麦场、道路的,霍霍然磨镰刀的,置买杈把、扫帚、木锨的,走起路来俨然呼呼带风;女人们则在家里拆洗、缝补,磨面、炖肉、蒸馍,洋溢在脸上的是笑容,表现在手上的是麻利。“龙口夺食”的喜悦之情,在忙碌中发酵着、蔓延着,摩拳擦掌迎接丰收的激情已然在心中燃烧。有姑娘出嫁或者新媳妇进门的人家,还要安排邀约亲戚们,一起给新亲家送花馍称为“送节”,用传统的仪式表达对新添人口的欣喜和祝福,期盼新人为家庭带来子嗣繁茂、五谷丰登、吉祥好运。“算黄算割”声声叫,吹响了麦收的号角,庄稼人开始每天都要去各块麦田巡视一番,算黄算割,黄一片割一片。
这种情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刚分田到户时的家乡尤为普遍。在我的家乡,夏收是忙碌的,也是隆重的。收麦祭祀、开镰收割、碾麦扬场、晒麦看麦、装翁贮藏,大人们都充满了神圣感,也饱含着对颗粒归仓的期待和喜悦。对于我们学生来说,能放十天的麦收假,是最让我们欢呼雀跃的了。一回到家,妈妈已经将我的活儿安排好了。割麦、拾麦时候扎手扎脚、又晒黑一层皮,碾麦扬场时麦灰飞扬,自然不会安排我去的,我的任务就是呆在家里做饭、干家务。偶尔也会让我到地里帮忙割麦、捆麦、拾麦穗。在紧张繁忙、跟打仗一样的收麦过程中,妈妈总要念叨粒粒皆辛苦之类的话,提醒我不要浪费粮食,要珍惜学习时光。等到爸爸把一口袋一口袋的麦子扛回家来,我就知道,我最惬意、最美好的时光来了。
爸爸早早就在离家较远的瓦窑口,整修好一块周围没有围挡、树荫的晒麦场,好让新收的麦子从早晒到晚。
在帮着爸爸把麦子搬到架子车上后,我把我要用的物什也都搬上了车:一只板凳,一把扇子,几本书,一杯水,有时候还拿上老师布置的作业。一切放置停当,爸爸在前边拉,我在后面推,咿咿呀呀的架子车就直奔晒麦场去了。
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汗流浃背的爸爸和我将麦子全部倒出来,用刮板转着圈儿将麦子全部摊开推薄,又用耙子搅匀散开,爸爸就拉着架子车走了,走了老远还不忘叮嘱我,过一会儿就要用耙子翻搅一遍。我远远地找一个树荫,靠着大树坐在板凳上,摇着扇子,开始我看麦的好时光。
书是我此刻最好的伙伴。《高山下的花环》一书、《七剑下天山》、《书剑恩仇录》的连环画,我都是在那时看完的。还有一本描写解放战争时期故事的小说,书名已经不记得了,也是那时如饥似渴看完的。一钻进故事情节,就忘了自己置身何处,忘了还要翻搅麦子。偶尔有邻居路过,喊一声:书虫女子,该搅麦了!把我从小说里拉出来,我赶紧扣下书,快速拿起耙子,匆匆转两圈了事。书里的时光过得真快,日薄西山前爸爸又拉着架子车来了,一阵紧张的铲麦、收拢、装袋,咿咿呀呀的车子就返程了。
晒麦场所在的瓦窑口是一座废弃的砖瓦窑场,周围都是麦田,前面的一条小路蜿蜒通向沟里。这天,正沉浸在书海中的我,偶然抬头,突然发现一条狗远远地从沟口走出来,本来就怕狗的我,顿时害了怕,甚至还将它想像成了狼;因为传说中的狼都是从此间出没。看看四周没人,我赶紧放下书,蹭蹭两下爬到了树上。等到那条狗已经走远,我才想起我居然第一次上了树,一个人趴在树上乐了半天。
回家后我把这件事讲给妈妈听。妈妈当即将重点放在了我所讲述的狼还是狗上,因为那里离村子较远,顾忌到我的安危,妈妈决定不再到瓦窑口晒麦了,改在自家院子里晒,哪怕多晒几天。这样的理由,爸爸也不好反驳,只叹可惜了自己花时间修整的晒麦场。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惬意的好时光就这样结束了。
现在家乡农村的学校已然没有了收麦假——很多的麦田已消失;虔诚、隆重的麦收过程早已简化,收割机轰隆隆直接颗粒装袋;孩子们恐怕也已经体会不到麦收的艰辛和喜悦。。。。。。。只是不知道那种神鸟,是不是还在黄拉拉的麦田上空,费力地叫着:“算黄算割。。。。。。算黄算割。。。。。。。”
如今久居城市,已经不知时节变换。但在每年的麦收时节,心头总萦绕着一幅画面:远城市人稠物穰,近村居山野风光。遍地收割忙,一派丰收景象。咱今儿将农夫当,拱步挥镰大干一场。趁早出门不用晒太阳,汗珠子依然往下淌。算黄算割声声唱,夸咱架势儿蛮像。归来一路闻艾香,黄酒罐旁醉一场。。。。。。。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