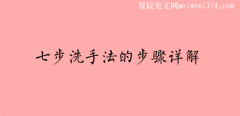当前位置: > 散文精选 > > 正文
一封没有寄出的情书
2019-09-18 02:23:40 作者:落花
我如约来到街角的咖啡馆,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不一会儿,一个熟悉的身影闪过,宋哥来了。我冲他招招手,他坐到我对面,冲我腼腆一笑,黝黑的脸庞上布满沧桑。
我给他叫了一杯咖啡,说:“谢谢你能来!”
“我得谢谢你,让我有机会把这件事说出来。”宋哥端起咖啡,轻轻啜了一小口,微微咧了一下嘴,似乎苦到他了。继而低头摆弄着自己手上的老茧。
“这件事压在我心里很多年了……”许久,宋哥仰起头,看向天花板,悠悠地说。
我和亚芳是同学,这你知道。她是一个积极向上、开朗活泼的姑娘,平时就很喜欢帮助别人,所以人缘特别好。我家条件不好,我母亲长年有病,不能下地劳动,就靠老父亲一个人地里刨食养活着我们一家四口,还要供我和弟弟读书。
屋漏偏逢连夜雨!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我母亲病情加重,地里又遭遇旱灾,种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眼看开学又要交学费了,父亲愁的蹲在地头儿放声大哭!我拉着父亲的衣袖说我不上学了,出去打工挣钱!父亲嚯的站起来,一脚把我踢倒在庄稼地里,两眼喷着火,怒吼着说:“你要过一辈子这样的日子吗?”我无言以对!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跟着父亲回了家。
天擦黑的时候,我正在给母亲煎药,听见门外有人叫我,出去一看,是亚芳。她手里攥着一把零散的纸票,说:“班长,这是我平时攒下的零用钱,还差两块就够你交学费的了,不过你放心,我交学费的时候会向家里多要两块的。”她把钱塞到我手里,转身就走了,任凭我怎么叫,头都没回一下。
简陋的病房里,亚芳坐在母亲床边,握着母亲的手,喃喃自语着:“娘,你快点好起来,你一定要好起来!”随之,窄窄的、瘦弱的脊背轻轻地抖动着,头也慢慢伏了下去。我轻轻敲了敲门,亚芳回过头,红肿着眼睛走了出来。
自那以后,亚芳就没来过学校了。

六月如火,高考如期而至。亚芳没有参加高考,我失落至极!回想着三年里的一幕幕,一桩桩,心乱如麻,最终我也“如愿以偿”地落榜了!
咱农村人,实在!不考学就结婚过日子。自从毕业以后,父亲便不断的托人给我说媒找媳妇儿,姑娘们一看我家破旧的房屋,生病的老母亲,还在上学的弟弟,纷纷打了退堂鼓。亚芳家自然是被媒人踩破了门槛儿的!但是亚芳心气儿高,一个也不应承。我暗喜,心里好像埋下了一颗种子。
那年夏天,我跟父亲在集上卖西瓜。时间还早,父亲去饼子摊买烧饼,我整理着西瓜摊儿。忽然,一声尖叫传来:“呀!我的钱包!”我循声望去,是亚芳,她站在马路上,慌乱的翻着身上所有的口袋,一遍又一遍。我跑过去,她看见我,先是一愣,继而眼泪刷刷的掉了下来:“我的钱全丢了!给我妈买药的钱……”我把她拉到路边,安慰着她。好一会儿,她才平静下来。我跑回西瓜摊儿,把钱兜里的钱全装上,又抱了个大西瓜。亚芳说什么也不要,我说:“不记得三年前的那把零钱了吗?”她一怔,半天没说话。我把钱塞到她的口袋里,说:“这下别丢了,快去买药!”望着亚芳远去的背影,我知道,心里的那颗种子发芽了!
回到家,没等我开口,父亲说:“小子,动心了?”我点点头,又摇摇头,父亲稍稍停顿了一下说:“试试吧!”“诶!”我高兴的答应着,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那天,下着雨,我躲在房间里看着书,父亲、母亲和隔壁婶婶坐在客厅里聊天。隐隐约约听到婶婶说:“姑娘虽然没说啥,架不住大人意见大啊!”
“咱这条件……也不能怨人家……”
“劝劝孩子,别想不开!”
母亲不出声儿,一声接一声的叹气。父亲“吧嗒、吧嗒”地抽着烟,一根接一根!我把书扣在脸上,闭上双眼,听着自己粗重的呼吸,任凭眼泪决了堤……
那年雨水多,西瓜并不好卖。看着板车里剩下的十几个西瓜,父亲说:“分了吧。”
天擦黑的时候,我把装好的四个西瓜搭在自行车上,往姑姑家驶去。去姑姑家路过亚芳家村子,她家就在大路边。我听着她家院子里呼哧呼哧的风箱声,亮开嗓门喊了一声:“西瓜嘞~”,风箱声戛然而止,我又喊了一声:“西瓜,大西瓜~”,不一会儿,亚芳走了出来,我把西瓜搬到她家门口,她看看我,笑了,那么甜,那么好看!
说到这儿,宋哥微微侧着头,目光平静而柔和,憨憨地笑着,沉浸在遥远的回忆里。
我们的事,最终还是被她父母知道了。父亲大闹,摔锅砸碗掀桌子;母亲大哭,绝食停药,以死相逼!亚芳拗不过,好长一段时间不敢见面。
突然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是亚芳寄来的,她说;在北京做生意的哥哥遇到点事,她过去帮忙,让我等她回来。我把信捂在胸口,紧紧地捂在胸口,生怕飞了!心里盘算着:等把麦子播上,我就去北京打工,顺便陪陪她。我奋笔疾书,把我的热情和思念一口气铺展在信纸上。这是我第一次写情书,用尽了所有的热情!
忙过秋收,我去集上买小麦种子,顺便把信寄上。在集市上遇到了亚芳的父亲。老人家看了我一眼,把我拉到一边,吞吐半天,终于开口说:“孩子,你是个好孩子,对俺妮儿有情有义,这俺心里都明白……可是……你说,俺家,她一个病妈,你家,也一个病妈!你俩要是好了,这……这日子咋过呀?俺就这么一个闺女儿,俺……俺是真舍不得啊!你也别怪叔,你俩……你俩还是断了吧!”望着亚芳父亲离去的背影,我的心,一揪一揪的疼!
没过几天,我又收到一封来信,望着被泪水打湿过的信纸,我心如刀绞。
自那以后,我离开家乡,跑去南方,做点小生意。后来,经不住父母的“软硬兼施”,便有了现在这个家。
一晃18年就这么过去了!
“啊……是!”我有点茫然。
“您好,我是亚芳的老公,我姓郑。”
“啊……您好!您……”我有些语无伦次。
“芳,不在了……走了……”
“啊?”我定在那里,手里的货物洒了一地,就像我散碎的回忆。
“芳,得了胃癌!五年的时间,我还是没有留住她……一个礼拜前,她走了,临走前告诉我这个手机号,让我告诉你,你要好好的……”对方哽咽着。
“哦……”我坐在地上,抑制着自己,“她……你们…………”
“我们有一个女儿,今年7岁。”
“嗯,好好把孩子养大……”我挂了电话。
那晚的夜很黑,天阴的很沉。我醉倒在城外的护城河边,没有人知道,那晚的酒有多烈,那晚的风有多冷,那晚的泪有多苦,那晚的心有多疼……
“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宋哥悠悠地说着,一串眼泪滚滚而下,像是说给我听,又像说给自己听,更像是说给远方听。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