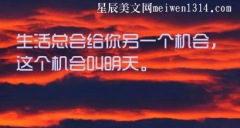奇怪的病
2023-05-16 18:36:04 作者:星辰美文网
人生故事奇怪的病
彭金山,是原市委市长,这不,他刚从二线退下来。
老彭哪儿也不去,每天,就待在家里,看看报纸,听听新闻,品品茗茶 。这日子一久,老彭可就憋不住了,处于一种职业习惯,总想找个人出出气,发发火。
这天,老彭的儿子下班回到家里,老彭说:儿子,去给老爸倒一杯水。
儿子不干,说:你整天闲在家里,啥事也不干,要喝水,自己倒去!
老彭一听,差点儿气出心脏病来:这儿子算白养啦。
过了会儿,老彭的女儿也下了班,老彭对女儿说:小霞,老爸口渴,给倒杯水。 老彭的女儿眼一瞪,比灯泡还大,不耐烦地说:你没有长手呀?凭什么对别人呼风唤雨?
老彭听了,伤心极啦,啪嗒从眼里滚出一颗泪珠, 足有豆粒那般大。
老彭心里不由得暗骂女儿:呸,不养闺女,义不过,养了闺女,赔本货,这话我算信了。
这时,老彭的老伴从莱市场买莱回来。
老彭想:俺俩结婚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相濡以抹,我说的话,她不会不听吧?想到这里,老彭决定试试老伴,就说:老伴啊,老头子我口渴得实在要命,这喉咙眼里直冒烟儿,劳驾你倒杯水过来。
哪料,老伴把嘴一撅,恨不得翘到天上去,说:你是谁啊?我怎么不认识你呀?是朝廷?还是皇帝?凭什么对我发号施令?
老彭流着泪,说;咱们可是老夫老妻啊!
老伴也懒得理老彭,只顾自已进橱房忙去了,把老彭一个人晾在那里。
老彭此时此刻是心潮翻滚、伏想联翩:自已在马上时,好不威风凛凛,春风得意,屁股往市长太师椅上一坐,不管是张三李四,还是王五赵六,谁敢不听他的!老彭唉地一声长叹,抽口闷烟,眼泪簌簌地往下流
一次,老彭上大街,想放松一下心情。
突然,老彭在一个岗亭前,瞧见一个年轻的交警,截住了一辆酒驾车,车主下了车,脸很红,显然是喝高了,但他偷偷地塞给那个年轻的交警几张百元大钞后,便被放行了,那是一辆豪华高级奔驰小轿车。
老彭悄悄地用笔记下了那辆车的车牌号码。
老彭走过去,严厉地批评那个年轻的交警,人家根本不尿老彭那一壶,还骂老彭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老彭非常不悦,他掏出手机,给市交通局的王局长打电话,准备投诉那个年轻的交警。谁知,电话不是没人接,就是关机。
老彭很是生气,一气之下,径自走进市交通局执法大队。
接待老彭的是大队长候囥,恰好市交通局的赵副局也在。
哟,彭市长啊,那阵风,把您给您给吹来啦?
老彭见有人喊他市长,心里如沐春风,一阵温馨,老彭说:谢谢你,还记得我,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赵副局笑着问:哦,是吗?您有什么事,我赵副局愿洗耳恭听,说吧。赵副局一听,劝老彭:老彭啊,这件事儿,你管得了么?你还是少操点心吧?
老彭很生气,说:我怎么就管不了啦?啊!我还非管不可!
赵副局说:你是谁啊?
老彭说:我是咱们市的一市之长呀!
赵副局问:是吗?那现在呢?我好像很清楚地记得,你已经从二线上退下来啦。
哦,是吗?
老彭一阵脸红,像火烧一样,觉着很烫很烫。
老彭垂着头,悻悻地离去了。
回到家里,老彭就生了病,躺在床上, 不吃不喝,两只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
这下可吓坏了老彭一家人。
老彭的儿子怕他有个啥好歹,赶紧送进了医院,拍cT,做透视,找专家,医生一检查,说人没病啊!
这时,老彭女儿小霞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在市交通局三中队上班的男朋友打过来的,电话里说,小霞,你还是劝劝咱爸吧,别让他老人家动不动就往市交通局里跑,净是添乱。前几天,领导找我谈话,说咱爸不该管一个值勤的年轻交警,那个年轻的交警知道是谁吗?他就是顶替咱爸位置的娄市长的亲侄儿,刚警校毕业的
老彭噌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吼道:我不管他是谁!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老彭的儿子突然想到了什么
翌日。
老彭的儿子说:老爸,你不如去儿子开的夕阳红度假村,当顾问吧,也好发挥一下您的正能量。
老彭一下子从床上弹起来:不,我要当董事长兼总经理,任何人都要管!其中,也包括你!
老彭的儿子笑啦:成!答应你。
老彭高高兴兴的去了。
老彭的病,不治而愈。
老彭活到九十九,才驾鹤西去。
幽默故事奇怪的病
今天下午我们公司发工资,还涨了许多,我一高兴,便把我的铁哥们大牛拉出来吃饭。
“什么事啊?看你这犯的得意劲。”大牛大口嚼着面前的荔枝肉,含糊不清的问道。
“哈哈!你兄弟我今天发工资,并且涨了许多!服务员,快上一箱啤酒。”我高声叫道。“来,我们今天不醉不归。”
“唉,兄弟,我…我可喝不了这么多酒。”大牛听到我这句话后,打了个哆嗦,忙说道。
“你喝不了?别跟我装,你不是人送外号‘不倒翁’的酒牛吗?”
“是真喝不了,我现在一喝这酒,手就会肿起来,可痛了。”大牛心有余悸的摸了摸自己的手,眼神躲闪的对我解释道。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你有这个毛病?说,是不是看不起你兄弟我?”我厉声问道,随即话锋放软,“其实,喝一点酒也没什么,你说的肿起来应该要喝很多才会那样吧。”
“这……”大牛还欲再辩解什么,服务员就把一整箱搬来,摆在了我的脚下。
“好了,什么都别说了,来,不醉不归!”我开了一瓶酒递给给大牛说道。
“好吧,不醉不归!”大牛看到了酒,似乎一下鼓起了勇气,一把将酒接过去,便“咕噜咕噜”喝了下去。
……
第二天早上,我伸了伸懒腰,摸了摸微微泛疼的头,忽然想起来昨天大牛对我说的话“……我现在一喝这酒,手就会肿起来,可痛了……”
好,打个电话叫他出来,看看是不是真的会肿起来。我心血来潮的想道。
“喂,大牛吗?今天周六,出来玩玩吧。”
“唉,是竹竿啊,都是因为你,我今天出不去了:我的腿肿起来了。”电话里传来大牛沙哑地声音。“哦,那个,不然你来我家坐坐吧,我老婆今天去超市买东西了。”
“嗯,也行,你不是手会肿吗,怎么脚也肿了?”我疑惑的问道,
“你来了再说吧。”大牛答道,“对了,还有,请多保重。”
……
“叩叩叩。”
门开了,眼前的大牛真是让我忍俊不禁:头上鼓起一个包,眼睛浮肿,右手严重淤青,左手好些,右腿似乎也肿的厉害,整个人看起来精神十分萎靡。“大牛啊,你这是什么病啊?看起来挺严重的,得治!”我笑着问道。
大牛没答我的话,而是悄悄向我说:“你还是回去吧,这,这病,会传染……”
“这是什么话?你是我兄弟,传染就传染,我可不怕,大不了共患难呗。来,让我进去。”我大咧咧的说道,并把大牛推开,走了进去。
“这病啊,还真奇怪,我头一次听说……”正走着,我突然感觉前面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我缓缓抬头,看见了一张凶神恶煞的脸——大牛的老婆。
“你想知道这病是什么吗?”大牛的老婆恶狠狠的对我吼道。“我告诉你,这就叫‘大牛喝酒回家就要挨打症’,而你即将得的便是‘拉大牛喝酒就要挨打症’!”
在我的惨叫下,我也得了一个我一生都无法治愈的“奇怪的病。”
睡前故事奇怪的病
绵羊妈妈有两个可爱的小宝宝:哥哥叫灰灰,长一身银灰色的毛儿,头上还有一对螺旋形的弯角,那模样儿可真神气!妹妹叫白白,乳白色的毛儿细软卷曲,垂挂着一对大耳朵,长得可真漂亮!兄妹俩天真活泼逗人爱,真是绵羊妈妈的心肝小宝贝!
小绵羊在长大。由于妈妈的娇惯,使他们变得任性不听话。
绵羊妈妈教育灰灰:“吃东西不能挑食拣嘴,不然会缺乏营养的。”
灰灰却把妈妈的话当作耳边风。他顶爱吃燕麦、干猫尾草和西葫芦,就尽挑这些东西吃,别的草儿却连一根也不碰。
绵羊妈妈又教育白白:“别到小河边那块草地上去吃草,听说那儿土质不好,长的草儿缺乏一种什么营养,老吃就会害病。
白白也把妈妈的话当耳边风。她想:“小河边的草地离这儿挺近,那儿的草又嫩又肥,只有傻瓜才到别的地方去找草吃呢!我可不愿意跑远路。”她天天都到小河边吃草,自己觉得挺聪明。
谁知道,过了一些时候,情况有些不妙。绵羊妈妈发现,她的两个孩子有些不大对劲:灰灰的毛儿越长越慢了,别的羊儿剪过毛以后很快又长长了,只有他好象不大肯长,而且毛儿变软,容易脱落。他眼睛、鼻子和嘴巴的粘膜失血,胃口不好,不想吃东西,变得非常消瘦、虚弱,连眼睛也失去了光泽。白白呢,更怪了!她原先经常蹦蹦跳跳,走起路来活泼、轻快,现在却摇摇晃晃的,经常跌倒。她那一卷一卷的毛儿变直了。人们批评这种羊毛质量差。
绵羊妈妈看到这情景,急得团团转,说:“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
大红马劝她:“别急,别急,你带他们找山羊大夫去看看,听说他的医道不错。”
绵羊妈妈听了大红马的话,就带上灰灰和白白去找出羊大夫。
山羊大夫仔仔细细地给灰灰和白白检查了一番,摇摇头,自言自语地嘀咕道:“奇怪啊!他们不发烧,身上也没有伤口,这是什么怪毛病呢?”他为难地对绵羊妈妈说:“对不起,我实在看不出是什么毛病,你们还是去找猴子博士看看吧!他什么都知道。”
绵羊妈妈只好又带着灰灰和白白去找猴子博士。
他们定过一个地方,看见一只小花牛和一只小黄牛正站在路当中嚼着泥土。绵羊妈妈连忙跑过去劝阻他们:“小弟弟,这泥巴怎么能吃呢?你瞧这儿青草很多,你们饿了就吃几口草吧!”
小花牛和小黄牛使劲地甩了甩尾巴,任性地说,“别管我!我不饿,不想吃草,只想吃这个!”
牛妈妈听到这边的说话声,赶紧跑过来,一看这情景,急得叫起来:“小花、小黄怎么又在吃泥巴!泥巴怎么能吃啊?口味变得这样怪,你们一定是得了什么毛病!”
大家一看,两只小牛都长得十分矮小,小花牛毛儿硬硬的,没有亮光;小黄牛也瘦得皮包骨头,身上有皮炎,毛儿脱落,变得稀稀疏疏的,很难看。
牛妈妈哭着说:“这可怎么办呢?我的两个孩子都得病了!”
绵羊妈妈赶紧安慰牛妈妈说:“别急,牛大姐,我正要带孩子去找猴子博土看病,你跟我们一起去吧!”
于是,他们六个就一起上路了。刚走一程,就听到后面有谁在喊:“请等一等!”
大家停住了脚,回头一看,只见一只小白鹅和一只芦花鸡正摇摇摆摆、气喘吁吁地赶上来,喊道: “请问,你们知道猴子博士住在什么地方吗?”
绵羊妈妈回答说:“跟我一道走吧,我们也正要去找他呢! ”
灰灰打量了一下小白鹅,说:“小白鹅弟弟,这一阵没见到你,你长胖了!瞧,连细长脖子都长粗啦!”
小白鹅苦笑着回答道:“哪儿的话!听说脖子粗是甲状腺肿大的症状,现在我正是为这毛病去找大夫的。”
白白也发现芦花鸡有些特别:短腿、短翅膀,骨头变形。不用说,她也是得了怪病!
他们八个又继续上路……
猴子博士给病人一个个做了检查,说:“你们病得不轻啊!”
大伙一齐说:“是啊,这病好怪!”
“其实,这不是什么怪病。”猴子博士眨眨眼睛说,“是因为缺乏营养造成的。”
病人们听了,都嚷嚷起来:“不对不对!我们天天都吃得饱饱的,怎么可能缺乏营养呢?”
猴子博士笑了,说:“你们缺的不是别的营养,缺少的是硼、锰、铜、钻、锌这些东西。”
大伙儿更惊奇了,又叫起来:“我们从来没听过有谁吃铜、吃锌的,那些玩艺儿怎么吃得下!”
猴子博士摆摆手说:“安静,安静!朋友们,你们别误解我的意思,我并没有叫你们去吃铜、吃锌啊!请你们听我慢慢讲:咱们跟人、植物一样,身体里需要各种各样的元素,其中有些元素需要量很少,叫做微量元素,像铜呀,锌呀。咱们必须从食物里吸收这些营养;要是缺少了它们,就会害病。现在你们都缺少某种微量元素:灰灰缺钴,白白和小花牛都缺铜,小黄牛缺锌,小白鹅缺碘,小鸡缺锰,所以你们就得了这样那样的毛病。”
经典童话奇怪的喷嚏病
河马伯伯得了一种奇怪的喷嚏病。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河马伯伯起床后,象往常一样,先把床单整理好,再把被子叠成一个豆腐状的方块,然后就准备出门去散步。刚出门,河马伯伯就觉得鼻子有点痒,紧接着就打了三个响亮的喷嚏。从此,河马伯伯就开始不断地打喷嚏。
“啊嚏”,“啊嚏”,河马伯伯不住地打着喷嚏。吃饭的时候喷嚏会把餐具打得“七零八落”,喝水的时候喷嚏会把水杯打得“落花流水”。
“啊嚏”,“啊嚏”,河马伯伯上街去买水果和蔬菜,喷嚏推翻了狐狸的水果摊,打翻了猪大妈的蔬菜柜台;“啊嚏”,“啊嚏”,河马伯伯走过小松鼠的家门口,喷嚏震破了小松鼠的气球房子。
“啊嚏”,“啊嚏”,河马伯伯在家里,喷嚏打坏了他平时最喜爱的,摆在客厅里的一把紫砂壶;“啊嚏”,“啊嚏”,喷嚏打坏了他的一支万能写字笔,也打坏了他时刻都离不开的,用来工作的电脑。
早晨,河马伯伯不再出门去散步;中午不再上街去买水果和蔬菜;晚上也不再象以前那样兴致勃勃地坐在电脑前工作了。
由于喷嚏的干扰,河马伯伯什么也不能干,什么也干不好,为此,他感到非常非常地苦恼。
“嘀嘀嘀-----”,“嘀嘀嘀-----”,在一个雨过天晴,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犀牛阿猛开着一辆大卡车运货,一不小心陷进了路旁的一个大泥潭里,无论犀牛阿猛怎么样努力,就是没办法把大卡车从泥潭里开出来,犀牛阿猛急得满头大汗。
正在这时,河马伯伯路过这里,看着那辆呆在泥潭里一动不动的大卡车,和急得满头大汗的犀牛阿猛,河马伯伯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他决定让自己威力无比的喷嚏,把犀牛阿猛的大卡车从泥潭中解救出来。
“啊嚏”,河马伯伯的第一个喷嚏打的大卡车摇了摇。
“啊嚏”,河马伯伯的第二个喷嚏打的大卡车动了动。
“啊嚏”,河马伯伯的第三个喷嚏把大卡车从泥潭中救了出来。
“好哇!好哇!”站在一旁的小动物们看傻了眼,一个个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犀牛阿猛感动的热泪盈眶,连声说:“谢谢您,谢谢您,河马伯伯。”
“不用谢,不用谢。啊,-----”奇怪呀,无论河马伯伯怎么努力,就是打不出喷嚏来。
呵,河马伯伯奇怪的喷嚏病奇迹般地消失了。
生活故事没病找病
一
几年前,张保卫下岗了,但他不愁不忧,成天乐乐呵呵。他说,男人四十一朵花;我这一朵鲜花才刚刚开放,不能就这样散了伙。于是,借钱,投资,包括硬件设施和技能培训,最后,成了一名食品工作者。他给自己的食品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不作为”牌烤地瓜。
这一天,一辆QQ轿车“嘎”的一声停在张保卫的炉子旁,下来一人。张保卫一惊:这不是“二头儿”吗?“二头儿”是张保卫以前的工友,官做到车间副主任,跟他一起下岗后,开起了出租“摩的”,可今天,怎么鸟枪换炮啦?张保卫拿起一块狗头般大小的烤地瓜,递到他嘴上。这“二头儿”也不含糊,呲牙咧嘴地吃了起来,边吃边说:“老伙计,愿不愿意长病啊?”
“喝高了?吃错药了?还是神经了?”张保卫冲他肩膀上捣了一拳。
“二头儿”又问:“稀罕不稀罕大钱啊?”张保卫摸了摸他的前额,说:“不发烧啊。”随即缩回手:“我两个爹两个娘,一个老婆俩孩子,吃喝穿住,还交养老保险,我不稀罕钱,龟孙子稀罕钱啊?”
“好哩!晚上,你请客哦,露天大酒店:生啤外加羊肉串!”
二
几天后,张保卫早早地来到医院,排队,挂号,然后一手捂着肚子,弓着腰,哼哼唧唧的来到内科诊室:“医生,救救我,我心脏病又犯了!”医生用手指顶了一下他的胸膛:“心脏在这儿哪。坐下!”一番望、闻、问、切,然后开了张单子:“去做个心电图。”张保卫在另一个楼层做完心电图,医生在报告单上写下结论:未见异常。
回来后,张保卫把看病经过跟“二头儿”说了,“二头儿”说:“嗨,你傻啊?下次,我跟你去。”
张保卫在“二头儿”等人的陪同下,又来到医院,医生又让他去做心电图。不过这次,“二头儿”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个真有心脏病的人,他把张保卫的申请单递进去,做心电图时,让这个心脏病人去顶替。这回,张保卫是“真”的得了心脏病了。
“二头儿”说,看病记录至少三次才行。第三次上,“二头儿”和那位心脏病病人又陪着张保卫来到医院,折腾了一上午,总算大功告成;可是,刚出医院门,那心脏病病人就发生了急性心肌梗塞,幸亏抢救及时,才保住了性命。
那病人家属冲着张保卫不依不饶。怎么办?掏钱呗:一年多的“不作为”牌烤地瓜,没了。好长时间,张保卫闷闷不乐。
三次看病以后,关键时候到了,这次,是有关专家来做鉴定。张保卫在“二头儿”的陪伴下,来到鉴定诊室。专家仔细看了他以前的看病记录,初步认为合乎要求,但必须再做一次心电图,不过这次跟以前不同,做心电图的地方就在这个诊室之内,有关专家和其他工作人员都在现场。
“二头儿”没辙了,雇来的另一个真有心脏病的人没派上用场,张保卫仍然是“未见异常”。
几番折腾,少挣的,多花的,半年的“不作为”又打了水漂,还招来了不少人的耻笑。
张保卫再不是那朵鲜花。他茶饭不思,入睡困难,行为怪异,口中的小曲变成了自言自语,不知所云;烤的地瓜不是糊了就是欠火。
妻子翠花安慰他说,算了吧,咱没那个本事,就别碗外头要饭吃了;一家人没病没灾的,这不很好吗?张保卫却不这么认为,他说,跟他一块儿下岗的,好多有门路的都在家享福了,比我这成天忙活的拿钱还多,显得我好像多么无能似的;再说,光凭咱那烤地瓜,猴年马月住上两室一厅啊?他说,“二头儿”鬼点子多,又有门路;你看人家,小车开上了,房子住上了;再去找找他,肯定还有办法。
三
好长一段时间,翠花发现,张保卫每天晚饭以后,就不知去向,很晚才回家;每次问他,他都是诡秘的一笑,然后做出一些怪异的动作,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这天晚饭后,张保卫又溜出去了,翠花偷偷地跟在后边,看他到底去捣鼓什么名堂。
城中村一个偏僻院落的房间里,聚集着十来个人。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时而手舞足蹈,时而发出尖利的怪笑;时而把柴草放在头上,时而又把衣服撕扯得七零八落,甚至脱得赤条条相互嬉戏、打闹。突然,闯进一个人来,拽着张保卫就往外走。回到家,翠花冲他吼道:“你疯了?到底要干什么啊?”张保卫听了,像是小学生受到了老师的表扬,说:“你看我疯了吗?疯了就好,疯了就好。”他说,他参加了“二头儿”组织的“疯人培训班”,经过培训,离一个真 “疯子”差不多了,说完,立马来了一个鬼脸。
翠花哭了。
又一次的病情鉴定会就要开始了。张保卫已经三个月没有理发、一个月没有洗脸了。这一天,他戴了一顶二十年前的破帽子,旧棉袄上扎一根草绳,大脚趾露在鞋子外。面对几个医生,他来了个先发制人:伸出脏兮兮的双手,挨个跟他们握手;面无表情的念叨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把他按在座位上,一个医生问:“你是哪一年出生的?叫什么名字?”张保卫麻利的立正、敬礼:“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医生在鉴定记录上写下:答非所问,认知障碍。又问:“你原先干什么工作?”答:“做官常为民做主,打回老家卖红薯。”医生又记下:思维混乱,逻辑性缺失。问:“你家里都有什么人?”答:“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萨达姆是我大姐夫。”医生又记下:妄想型语言,妄想型心理。鉴定组组长在鉴定书上写下结论:精神分裂症。
四
张保卫顺利过关,就等着好消息了。“二头儿”也大功告成,拿到了不少的劳务费;下一步,就是找他在关键位置上的表哥,进一步运作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关部门发了文件,其中有这样一段:鉴于本次病情鉴定中,焦虑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患者弄虚作假者甚多,而本病种又无客观指标界定,故以上病种的鉴定结论一律作废。
张保卫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不过这次陪他去的不是“二头儿”,而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医生说,他患了精神分裂症,有一定的自残性和攻击性,需要住院,限制行为,正规治疗。
又一次的病情鉴定会开始了。这次,有关专家来到精神病院现场办公。
张保卫实现了他的梦想:和有门路的下岗工友一样,办理了“病退”手续,只不过他办的,是货真价实的手续。从此,他不但免除了每月缴纳的养老金300元,还能领倒500元的退休金。可是,附近居民再也吃不到他那又酥又甜、香喷喷的烤地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