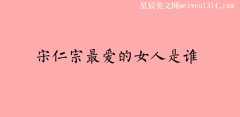当前位置: > 心情随笔 > > 正文
螳螂
2019-08-28 01:38:03 作者:柳槐

这是我二十二年来,第一次见到螳螂。
所以我断断想不到,有一天我会见到一只螳螂。
因为我没见过螳螂,所以我也不知道螳螂会飞。我只知道螳螂结了婚会吃了自己老公,以及,螳螂会打拳。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当我在五楼的阳台看书的时候,被台灯吸引来的可能是任何会飞的昆虫,但绝不可能是螳螂。
所以我断断想不到,有一天我会见到一只螳螂,而且,是在五楼的窗外。
玻璃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的规律。可以想见的是,在玻璃出现之前,世界上应该有这么一个原则:凡是可以看到的,必然是有可能触碰到的。时至今日,对于从未见过玻璃的人,或者,无法理解玻璃的动物来说,这应该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所以我看到它的时候,它盯着我桌子上一株早几步入秋的文竹,奋力的挠着窗户。在他看来窗框绝不是个框,顶多算是一个门槛,迈过去,也就迈过去了。
人是万物之灵,所以我也是万物之灵,因此我决然是不会挠玻璃的。
不挠玻璃,就是我的祖辈们一代又一代进化后赋予我的优势。这个优势看起来很小,不挠玻璃罢了,但是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优势。因为我看着螳螂的时候,螳螂也在看我,除非我吃掉它,或者我踩死它,否则我按理来说是不可能和他建立客观的食物链地位的。
我看着它,他看着我。我不吃他,他也不吃我。我不踩死他,他也不踩死我。
螳螂就是我,我就是螳螂。如此这般,人命几如蝼蚁。
好在,它会挠玻璃,而我会,但我不愿。
于是它在挠玻璃,我不挠玻璃,我能看它挠玻璃,它不能看我挠玻璃。
我在它眼里是一个硕大的捉摸不透,他在我眼里,是一个小小的一眼望穿。
我们双方互不打扰,也没有人受到伤害,但是通过一面玻璃,我轻而易举就能巩固起我食物链的地位。
什么是文明?这就是文明。
所以我花了十分钟,一动不动,看它挠玻璃。
它也不是一刻不停就在挠玻璃,毕竟万物有灵,它在几次尝试之后就知道力有不逮。所以有那么几次,我看到它转过身去,尾巴对着我,想要找一个退路,离开这个捉摸不透的玻璃。
但是我家在五楼,虽然我不知道它是怎么飞上来的,但是我能想到的是,它从五楼往下看,内心应该不会非常平静。毕竟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认识里,螳螂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吃老公,二是打拳。人对于飞有一种奇妙的向往,所以任何会飞的东西,哪怕是苍蝇,我们也会把“它会飞”这个认识,深深的种在脑海里。但是螳螂,起码对我来说,飞,不是它的标签。因此可以想来,它至少是不善于飞行的。
五楼对他来说,可能近似于一个几百层的高楼之于我。
所以它很快就会掉过头来,继续挠玻璃。
大概在他第四次休息的时候,我起了恻隐之心。我觉得,既然它是能飞上来的,那么即使真的从五楼掉下去,应当也是摔不死的。从我的窗台跳下去,不能算是跳楼,可能更像是某种翼装飞行。
我也不必一定是一个看客,我还可以是一个蹦极台的工作人员,负责在游客不敢跳的时候,推他一把。
所以我打算,推它一把。
然后,我很用力的砸了一下玻璃。
住惯了寝室以后,人会对自己的家也产生一些错误的判断。
比如我在寝室的时候,楼下施工,就算我关上窗户,噪音依旧很大,所以我在家听到施工的声音会想不到可以关窗,全然忘记了吉利的窗户除了有橡胶隔音条外,还有一个隔音的真空层。
这种忽略不是一种特定情形的忽略,而是一种彻底的、全面的忽略。
比如我也会忘记,真正厚的玻璃,被用力砸过之后能带来的震动其实非常有限。
所以它并没有被我砸落,只是依旧在窗外挠着玻璃,而我在它眼里,可能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在看了几分钟以后,终于学会了该如何挠一挠玻璃。
于是我看着它,他看着我。我不吃他,他也不吃我。我不踩死他,他也不踩死我。
我看他挠了玻璃,它也看我挠了玻璃。
螳螂还是我,我还是螳螂。几来几回,人命终究还是一如蝼蚁。
所以我也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不再看他的,等我看完了政治,做完了选择题,整理完了知识点的时候。它早已经无影无踪的。
它也许爬去了邻居家的窗沿,也许终于鼓起了勇气从五楼一跃而下,或者,它可能飞上了六楼,或者是七楼。
但是无论如何,它毕竟是长着翅膀的,八月末的兰州没有大风,我们小区不大的院子也养不活什么黄雀。所以它应当活的很好,起码好过我身边枯多荣少的文竹。
可想而知的是,这可能是我和它这辈子最后一面了。
毕竟我被我的远大前程囚于斗室。而它终究属于自由。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