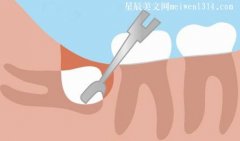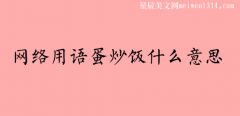那份源自母亲的爱作文850字
2020-12-25 23:03:57 作者:英宸瑞
突然,一块突起的砖头绊倒了我,母亲撩起裤腿,看到的是:“没事儿,就是擦破皮儿了。”而我看到的是:“啊呀,都破皮儿了!要不要去医院啊!”母亲却说:“破个皮,去什么医院,是不是男子汉!”
我跟在父母后面,又委屈,又闷闷不乐,感到我做男子汉的自尊心受到极大打击。
“哎呀,我自己去吧。”我不耐烦地说。
说罢便飞也似的出去了,跑步时一直在回味母亲的话,她的白发慢慢生根、蔓延,而我却不耐烦地敷衍她……
“咣!”我狠狠绊在井盖上,身子腾空出去,还好用手撑住,再一看腿,已卡了大大一片擦伤,鲜红鲜红的。
我早是个大男子汉了,用手一撑,跳起来,又慢悠悠地跑回家。
我泰然自若地进了门,母亲一进门就问:“第一次跑步咋样?”我说:“没啥事儿,就卡了一跤。”说罢一挽裤子,鲜红已变殷红。
“卡得这么严重啊!”她脸上露出一股关怀。“妈给你上酒精吧,要不要去医院呀?”
那个问“要不要去医院”的人变成了母亲,而回答“没啥事儿”的人变成了我。“我自己上酒精”,说罢立刻进屋,往床上一坐,又想起母亲的那番话,那番关怀,那些白发。
“妈,你给我上酒精吧。”
母亲推门进来,脸上流露着惊奇,还带三分怀疑,乐呵呵地取出酒精,蹲在我身边,用棉球一沾、一敷。
一股剧痛向我袭来,虽然痛,但我不想叫出声,只是把脖子向后仰,尽量装出一副轻松的样子,怕母亲看出来而担心。
可我还是没能如愿,母亲脸上布满了担心的神色,嘴微微张开:“儿子,疼吧。”眉毛皱成一团。
“不疼,不疼,暖暖的。”
我的心里也暖暖的,像有什么在涌动,我恍然大悟:那涌动的是源自母亲的爱。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