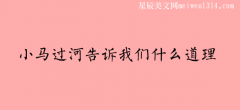当前位置: > 读后感 > > 正文
曹禺传读后感
2019-11-20 15:05:05 作者:耿世涛

现代文学史上,一向有“鲁郭茅巴老曹”之说,其他几位的排名要靠前一些,名气也要高于曹禺。然而,正如人们常说的,“武无第二,文无第一”,你很难严格地为他们排名,即以不在其中的沈从文来讲,其作品数量和质量也未必在这六位之下。但是,单以戏剧这种文学形式的创作而言,曹禺绝对是要排第一的。文如其人,曹禺的人生是充满戏剧性的,而他的戏剧也很好的展现了丰富的人生,这是读《曹禺传》给我留下的最深体会。
记得谁说过类似的话:想要成为作家吗?给他一个不幸的童年。正和许多大作家一样,曹禺的童年是不幸的,尽管生在万家这样的封建官僚家庭,住洋楼,雇仆佣,生活优裕。但曹禺出生后三天,其生母薛氏就因产褥热离世,这在小曹禺的人生中埋下了深深的苦闷的种子。曹禺母亲去世后,其父万德尊怕别人带不好孩子,特意把小姨子薛咏南(也就是其母薛氏的孪生姐妹)从武昌接来照顾他。姐妹俩长得一模一样,而薛咏南不久也嫁给了万德尊,成为曹禺的继母。这位既是姨妈又是继母的薛咏南一生没有生过孩子,把曹禺当自己儿子看,然而这也不能填补幼小心灵的缺口。他常说:“我从小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心灵上是十分孤独寂寞的。”这种孤独与寂寞是伴其一生的,直到成为70岁的老人,一提到生身母亲,仍是无限的怀念和伤痛。
曹禺的童年让我想起芥川龙之介和列夫。托尔斯泰。芥川的母亲芥川富久在他出生后八个月精神失常,10年后去世;其姨母芥川富纪一生未嫁,像生母一样呵护养育龙之介。但是生母发狂、为人养子也让其终生背负精神的负累,为此苦恼不已,也养成了神经质的禀赋。我最最热爱的列夫。托尔斯泰也是幼失怙恃,直到暮年还紧紧怀抱自己的双膝,找寻母亲的温存。厨川白村说,艺术是苦闷的表现,文艺是苦闷的象征,苦闷培养了一颗敏感孤僻的心,也孕育着文学的种子。他们的作品都可以说是苦闷的宣泄,都对人性有着惊人的体察与把握,我想这与他们童年的不幸不无关系。
孤独的灵魂更需要伴侣,在爱情上,曹禺是执着的,浪漫的,耽于幻想的。在清华时深深地爱上了一起排戏的郑秀,并开始了狂热的追求。曹禺有多狂热,田本相是这样写的:
在一起排演《罪》的日子,那恋爱的情火便越烧越旺。一旦爱情迷住了他,他就像个充满稚气的孩子,也像他念书那样痴迷。他经常跑到女生宿舍——古月堂外边守候着郑秀,有时夜晚也徘徊在楼旁的小树林里。他爱得那么执着,那么天真。在爱情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一宿一宿地守在那里,望着郑秀宿舍的窗子……
尽管郑父反对,两个人性格志趣脾气上也有不同,时常争吵,但一对浪漫的年轻人还是在困难中结合了。两人后来在长沙,在1938年抗战热潮中结合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有人都看出二人的结合并不合适。当时参加他们婚礼的吴祖光这样回忆说:
曹禺为什么要同郑秀结婚,我都感到奇怪,他们的生活习惯、思想境界毫无共同之处。在清华时,他追郑秀追得发疯了,清华有树林子,他们一起散步,当回到宿舍时,却发现近视眼镜丢了,丢了都不知道,真是热恋,是沉浸在爱情之中了……
曹禺的后两段婚姻传记中言辞含糊,所言不详。查了些资料才知道他与方瑞经过10年的婚外情,于1951年结婚。后来方瑞于1974年过量服用安眠药去世,他于1979年与李玉茹结婚。而郑秀,自始至终对曹禺一往情深。这当中曲折谁能说得清楚呢?这又让我想起芥川龙之介对作家佐藤春夫的话:“造成我一生不幸的,就是……(指为抚养自己终身未嫁的姨母)。说来她还是我唯一的恩人呢。”因爱成恨,彼此伤害,这也许是人性的不解之谜。
曹禺的人生是如此富于戏剧性,而其一生也始终与戏剧相伴:儿时天津卫看戏,少时南开中学排戏,后来在大学写戏、演戏、教戏。可以说,曹禺是为戏剧而生的,而戏剧也体现了曹禺的人生。
曹禺一生戏剧活动中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技巧,而是在戏剧中对人,对人生和对人性的体察以及对人道主义的体现。他赞美莎士比亚的戏剧:“就像泉水那样喷涌而出,每个人物,哪怕是一个乞丐,一个流氓坏蛋,一个王侯,说出来的台词,时如晶莹溪水,时如长江大海,是宇宙与人性的歌颂,是用利刃解剖人性的奥秘,是寻常却永恒的珠玉,是阳光灿烂的人道主义的精华。”我想这也是他追求的目标。
他的戏剧中,对人性的假恶丑总是报以鞭挞。他关注着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并报以深深的同情。他说:
我在太原看到的妓院,那些妓女是被圈起来的,她们的脸从洞口露出,招徕嫖客。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副惨相。在北京西直门一带,天津三不管、南市都有这样的妓院。像太原的这种妓院是最低级的,整天接客。那样,不到几个月就会死的。这是我最早见到的妓院惨状,那种惨象真是叫人难过极了。我后来写《日出》中的第三幕,那不是最低级的。后来,我到了四川,最惨的是重庆的花街,十字的街道,每个街口都有流氓把守着,每个街口进去都是卖淫的地方。十字街里有许多水坑,妓女得了花柳病,快死的时候,喝着水坑的水死去,实是叫人目不忍睹。就是这次太原之行,看到妓女的惨状,才激我去写《日出》,是情感上逼得你不得不写。
他借剧中人物的话强烈控诉了社会的不公,鞭挞人性的丑恶,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闪烁万丈光芒:
有钱的大爷们玩够了,取了乐了,走了,可是谁心里的委屈谁知道,半夜里想想:哪个不是父母养活的?哪个小的时候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哪个大了不是也得生儿育女,在家里当老的?哼,都是人,谁生下就这么贱骨肉,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日出》中翠喜台词)
他对生活的体察细致入微,为搜集素材甚至有点不计成本。书中多处所记载这样的细节:为学数来宝数九寒天半夜混进贫民窟等两个吸毒的乞丐而遭老拳,险些被打瞎一只眼睛;江安剧校任教时跟踪观察当地大地主黄久安而被怀疑;坐在做豆腐老婆婆店前连续观察三天……这些都给人莫大的启迪:天才的背后是辛勤的汗水,出神入化的技艺背后往往是艰辛寂寞的劳作。
曹禺演出过很多戏剧,早期男扮女装的娜拉,自己作品中的周朴园,但他的告别演出是1942年出演《安魂曲》中的莫扎特。这是怎样的阵容:张骏祥、焦菊隐、曹禺三位戏剧大师的合作。曹禺本人对莫扎特这一角色也是全身心去阐释。他说:
演到莫扎特生命的最后一息,似乎连自己的生命和灵魂都来了一次升华。我喜欢这出戏,我喜欢莫扎特这个形象。写一个角色和演出一个角色都要用自己的心灵去创造。我演得不够理想,但我确是用我的全部心灵去拥抱这个角色。演过这出戏之后,我再也没有演戏了。
曹禺说得谦虚,当时的演出是极其成功的,博得观众的强烈反响,陶行知观看演出后泪流满面。因为“在莫扎特这个人物中,他注入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注入了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水乳交融地流泻着、迸发着。是这样的,他使这个人物有了深度”(刘念渠)。
一个杰出的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一个用灵魂演出的演员,一生只演一个角色(如陈晓旭、保罗。沃克)。他们在戏剧中找到了自己,把生活升华成了一出戏。曹禺,也许正是在莫扎特身上找到了自己,从而超越了生命的苦闷。且看莫扎特最后说了些什么,这也许就是曹禺的心声: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