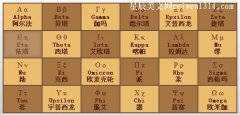当前位置: > 情感日志 > > 正文
童年的电影
2017-04-07 00:14:28 作者:星辰
腊月廿八晚上,我们就躁了起来,上蹿下跳,惹得左邻右舍纷纷开了窗户探头骂,军人们在廿八晚上来帮我们布置场地,当然,更多的是陪我们玩儿。那时对电影的念想之中,绝大一部分是为了他们,大概是因为能和童年的我们搭在一起的大人只有他们,更是因为,在那个年代,驻守的兵哥哥对于我们来讲,是无所不能的神。
年三十晚,各家各户都很安静,孩子被大人早早地赶上了炕,把我们哄睡,如若有谁不听,便会威胁,明儿不让看电影,那对当时的我们是多大的惩罚啊!便都一个个利落地翻身shangchuang,生怕大人们不让我们去看电影似的。
历次电影是很老套的抗战剧,枪声轰轰作响,“噼里啪啦”的声音让我们应接不暇。
年初一晚上,左右的街坊领居三五成群来了,熙熙嚷嚷的,驻守的军人们也来了不少,放眼一望,只叹如同一幅精妙绝伦的画卷,人来人往的土地上,有一种归属感在慢慢地延伸。
果不其然,那熟悉的枪炮声又一次萦绕耳畔,我们几个“好动分子”不安起来。

老北京有句话:“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我们这群孩子,倒也应了这句话,只是我们一年只揭这么一次瓦,大人也就随我们去。
上屋顶去的,倒也不干啥,就这么躺着,躺着看底下的电影,许是上头的空气比下头好,许是躺着比坐着有味道儿。不多久,几个大人也利落地攀了上来。(星辰美文网wwW.mEIwen1314.CoM)霎时间,只觉得有一股神奇的魔力,电影变得更好看起来了,我们就这么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幕,也说不上它在放什么。
直到夜深,画面被定格在战火中浴火重生的东方大地之上,我们才如梦初醒,伙伴几个对视一眼,趁大人不注意,“solo”一声跳下去,直惹得大人惊叫连连,这才心满意足地朝家走去,“年度盛会”就这么落幕了。
不知什么原因,多年以后,面对多少“大咖巨献”“XXX倾情制造”的大电影,我竟提不起一点儿兴趣。
那幕布有多少次光顾我的梦境,我已无从得知,只记得,后来的日子里,我绞尽脑汁妄想寻到那幕电影,可惜物是人非,再也不见了。
我仅存的回忆,跟着建篷的长杆儿一起,被埋进了无尽的黑土地中。
多少次的午夜梦回,那白幕仍令我流连忘返。那光彩仍旧令我“怦然心动”。我多少次竭力追寻它们遗下的痕迹,那记忆,却是早已混着泥土的苦涩,被填进了那熟悉土地上的水泥路里。
那远归的电影,如同我飘渺的童年一样,到头来,都成了——一场梦。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