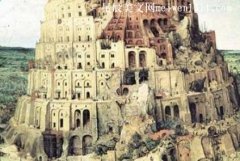当前位置: > 散文精选 > > 正文
一窗阳光
2018-11-09 22:16:31 作者:蒙鹏
门开了,黑隆隆的。眼睛好一阵子才适应过来。原来,这是个过道。我和房东摸着前进。打开东北角的房门时,整个世界都亮了。
房内有一张单人床,一小张破桌子。此外,什么也没有。窗子很大,几乎占了一堵墙的位置。没有窗帘,阳光正肆意的照进来。窗外是深不见底的峡谷,远处是青山。原来,这是城市的边上,房子从半山上砌上来。
原来这是套房,每间卧室租给了不同的人。房东打开的那间是次卧。客厅用几块木板隔开,靠窗的那边也住了人,另一边算是过道。过道里的灯坏了,或是根本没有安装,我不知道。总之,过道一片漆黑。
房东又带我看了厕所,正对着次卧。开了厕所门,一股尿骚味扑鼻而来。开了厕灯,厕所里阴暗、狭小、潮湿,蹲便器上满是黄褐色的尿垢。房东说:“水在厕所里接。”厕所里,过道上,湿漉漉的。
考虑到我一人居住,不开锅,离单位也近,步行两三分钟就到,最主要是冲着那一窗阳光,我便毫不犹豫的定下了。毕竟,合适的房子并不好找。
我和哥去买了脸盆毛巾,牙膏牙刷,床单被罩,被子枕头。没有书桌。我找了两个背箩将单位楼道里废弃的办公桌搬了回来,放在窗前。看书写字,有了个依凭之处。如此,没有人否认,这不是个家。
这屋子原来住过人,将来还会有人住进来。对于这间屋子,我只是匆匆过客。但是关了门,开了窗,这里的空间,包括这一窗阳光,半缕清风,便暂时为我所有,听驱使。
这里很静。除了上下班的时候,偶尔有几声响动外,其余时间都是静悄悄的。让人感觉这房子全是空着的,没有人居住。邻居们除了碰见打个招呼外,白天外出各忙各的,晚上回来就把门关上,很少来往。
我没有挂窗帘。因为楼高窗旷,没有隐私。窗子朝东偏北,得日最早。但是,我似乎没看过一次日出。因为我睡得好。不是晚上起夜时,大地还在沉睡,就是我醒来时,太阳已经晒着屁股了。
夏日里,我常常被阳光晒醒。睁开眼来,墙壁上撒着金晃晃的光线,太阳已离开了对面的大山,把周围都照射得金灿灿的。我靠在窗边,望着太阳和远山,贪婪的呼吸着没有污染的空气。

虽然日出难遇,但晚霞却常见。那晚霞染红了对面山坡上的天空,变化莫测,漂浮不定。太阳在晚霞中穿行,向山的那边坠下去。后来,只留下一片通红。最后,大地归于沉寂。我看着太阳隐去,就像看着情人远去,有些无可奈何。
有一天,我路过大十字,看到有人卖花。我爱花,但是我不善养花,也没有养花的打算。我怕我养不好花,辜负了花朵的美好。那天,我停下了脚步。挑挑选选,在卖花人的推荐下,买了一盆仙人球。
我把仙人球放在窗前太阳直射的地方。记起来的时候,就浇点水。其余时间,我似乎忘记了它的存在。有一天,我惊奇地发现,仙人球朝阳的一面,似乎要长得快些。于是,我定期给它变换位置,让它长得圆些。
过了一段时间,花钵里还长出了一些小草。那小草越长越高,青翠的招展着,自由的吸收着阳光和水分。我说:“把它扯了吧!”妻子说:“留着吧!”经妻子提醒,我才感悟到,这些小草,只要给它一点阳光和水分,它就能努力生长。这是生命的力量。
搬家的时候,我将仙人球带走,放在了电视机旁边。过了一段时间,小草死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仙人球也死了。我不知道,仙人球和小草,是因为熬不过冬天的寒冷,还是因为怀念那一窗的阳光,像约好似的,双双返回了大地的怀抱。
直到现在,我还在怀念那一窗阳光,以及曾经给我带来惊喜的仙人球和小草。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