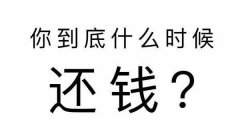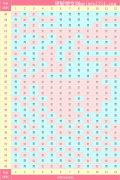当前位置: > 散文精选 > > 正文
“雌黄盖”的悲剧
2018-12-28 15:02:38 作者:儒雅
去年秋,托人购得雏鸽两对,一对名曰牛毛黄,另一对名曰黄盖。牛毛黄,羽毛色如黄牛;黄盖,羽毛黄中透白,头顶黄帽,甚是可爱。
我是不喜欢养鸽的,怕脏。
喂过鸽子的人都知道,鸽子一窝产蛋两枚,孵化期二十八天左右 。产蛋、孵化到小鸽出窝约四十五天。每窝一雌一雄,小鸽一般长到四五个月便可产蛋,是天生的一对。
刚买来时,这两对鸽子还没有满月,不会进食,我只好一只一只地掰开嘴,强行喂它们。两个星期后,它们才逐渐地能吃些颗粒较小的小米、小麦等谷物。有一点鸽子与鸡不同,它们非常喜食豆类,可鸡从来不吃。传说豆子是鸡的舅舅,很是可笑,可笑归可笑,真的没人见过鸡吃过。冬去春来,经过一冬的喂养,两对小鸽羽翼丰满。每天清晨双双划破曙光飞向蓝天,成为我心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说起风景,那比得上小时在陇东巴家咀的鸽子,那全是野鸽子,一群一群的,飞起来黑压压的一片,遮天盖地。我在那住了六年窑洞,哪里有我童年最美好的记忆,哪里有我小时候最要好的小伙伴,如大伍、黑蛋、陈胖子。哪里是黄土高原,山却不高,因长年天旱少雨,山坡上总是光秃秃的,记得生长最多的是酸枣树,也有刺槐,即洋槐树。每到冬季,白雪皑皑,成群的野鸽子以槐籽为食,在老家从没有见过野鸽子。前年出差途经武安、涉县时,偶尔看见天空掠过一群野鸽子,甚是惊喜,它们浑身灰色,脖子上如镶嵌一圈深紫色羽环,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光泽。野鸽子形似家养的瓦色鸽子,个子比家鸽小点,象“春咕咕”一般大小,也就是斑鸠。斑鸠在家乡常见,一到开春,它们就开始“咕咕”地叫个不停,怪烦人的。

今年春天,雄黄盖走路时不小心,爪子被细线缠绕了,行动笨拙,不能与雌鸽比翼齐飞。可雌鸽却不甘寂寞,总是独来独往,飞进飞出,对雄鸽黄盖不屑一顾。有时早晨迎着朝霞出去,晚上披着星星归来,好不自在;有时我发现它白天出门,夜里也不归宿了。我心里很是不安,常嘀咕它去哪了?迷路了?被人逮住了?这样可不行,总有一天会丢失的。我开始实施第一套方案,准备等它归巢时,一举抓获,关它“禁闭”,让它安分守己些。雌鸽仿佛察觉了我的动机,警惕起来。白天落在房脊上转上一圈,然后又飞走了。隔了两天,它竟领回来一只雄白鸽,这白鸽体大,羽毛丰满,色如白雪,煞是招人。雄白鸽时不时地围着它大献殷勤,“咕咕”地叫着,象在炫耀自己的美丽。我这才豁然开朗,雌黄盖夜不归宿的缘故,它另有所爱了。一日,雌黄盖又带着大白鸽归来,轻盈地落在房脊上,我视而不见,待到夜深人静,我一网扣去,如水中捞月,反倒惊吓了它们,一连多日没有了踪影。
孩提时,在陇东常常逮鸽子,皆是野鸽子。每到冬季一片白雪茫茫,山白了、树白了,不见陆地,鸽子寻不到食物。这时选一块野鸽子经常出没的地方,如山腰、盘山公路边的槐树下,我带着小妹、黑蛋、铁蛋等几个小伙伴去下鸽子套。鸽子套极简单,将十几根十公分的尼龙细线,系成活扣拴在一条麻绳上,在雪地上划一条二指宽小沟,先将麻绳两头用铁钉固定好,用雪重新掩埋,然后,将活扣一一摆在雪面上。再在雪地上撒些槐籽,玉米或小麦之类的食物,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便撤离,躲在不远处静静地观望。不一会鸽群“哗哗”地飞来,心里按捺不住一阵激动。鸽子走路一晃一晃地接近“雷区”,当它们见到食物,一轰而上地疯抢,在混乱中总有一两只倒霉蛋被套住,它们不由地拔“脚”,我们几个小伙伴见鸽子上套了,纷纷跑着喊着叫着:“套住了,套住了”,冲向鸽子。鸽子受到惊吓拍打着翅膀,越是拍打着翅膀活扣越发勒得紧,准没得跑。取下鸽子,打扫战场,重新布阵,躲藏隐蔽,不久鸽子又来……那年冬季,我一共逮了四十九只鸽子。开始抓到一两只先养起来,母亲见多了就说:“不少了,都饿瘦了,今天给你们解解馋”。而后,让我宰杀鸽子。宰鸽子最简单不过了,用食指和中指夹住鸽子脖子,用力一甩,鸽头与鸽身立马分家。母亲光取鸽胸脯,给我们炖上一锅香喷喷鸽肉。在七十年代,猪羊肉虽便宜三毛伍分一斤,可吃时很少,一锅鸽子肉,真是让我们开了荤腥。俗话说:“好吃莫如天上飞禽鸽子、鹌鹑,地下走兽数狗肉。”这些年很少吃鸽子了,真想逮住那只大白鸽,美餐一饨。
自雌黄盖和大白鸽那夜逃离后,雄黄盖整日心事重重,闷闷不乐,常在院中发脾气,惹事生非,渐渐地对雌牛毛黄产生了爱意,不断地去追去撵骚扰,颇是痴情。起初,雌牛毛黄躲躲闪闪,东奔西跳不理它,后来懒得动弹,索性往那一卧,任它啄这啄那,不几天,真的获得了雌牛毛黄的芳心。两只鸽子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害的雄牛毛黄在一边“咕咕”地不停抗议。一天我动了恻隐之心,也怕下一代基因不纯正。将牛毛黄双双强行关在了一起,真有点捧打鸳鸳之嫌,真有点捆绑难成夫妻之感。几天后,雌牛毛黄不知咋钻出笼子,又和雄黄盖粘上了,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母亲去世后,我的心情也很沉重。昨日,武安的三哥打来电话,约我去他那玩几天,我也想出去散散心,换一个环境轻松一下。五天后回到家,却不见了雄黄盖。父亲无奈地说:“卖了,也不成对,留下也没用了”。我一阵婉惜,毕竟是我一手“拉扯”大的,很是留恋。
时间如流水,一晃半年过去了,在一个雨后的清晨,我忽然发现雌黄盖又飞了回来,一阵惊喜,我忙抓起一把黄豆撒在地上,可它神情呆痴,一动不动,我这才发觉它遍体鳞伤,羽毛也脱落了许多,看来那只“白马王子”把它给甩了,也许那只大白鸽早已有家室,哪里没有了它的安身之地。所以它又回来找雄黄盖了,可雄黄盖在哪?已无人知晓。
唉,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竟落得如此下场,甚是悲哀。
相关推荐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