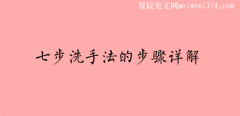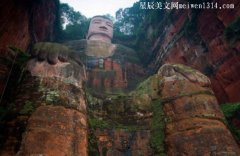当前位置: > 散文精选 > > 正文
那年冬天-关于冬天的散文
2019-02-25 19:33:14 作者:华山论剑
清晨的阳光照在雪地上,格外的刺眼。爷爷安排小叔清理院中的积雪后,就背起箩筐走了,我知道那一定又去拾粪了。那个年代汽车是个稀罕物,就连拖拉机也少的可怜。爷爷家住在路边,不知从哪里过来的驼队和运输的骡马日日路过门口,那规模甚是壮观。从西河到鼓楼叮叮当当的驼铃,唱响着走西口的情调,惹的我每次都要从头看到尾,满有点迎接客人的感觉。爷爷是个非常勤快的人,他说冬天是拾粪的最好季节,那时天寒地冻,牲畜的粪便很快就会冻成一坨,每天从家门口到西河一个来回就能拾一筐,堆在后院的空地里,一个冬天下来,足够地里上肥的。我那时不懂这些,只是习惯而已。那时冬日的雪下的很厚,却依然挡不住爷爷外出拾粪的脚步。
爷爷出了家门后,叔叔就哄着我和他铲雪,说是干完了会给我堆雪人,还要放炮。雪人倒无所谓,放炮却是极具诱惑力的。那时家里穷,过年买的鞭炮要拆下来一个一个的放,抓一把装在口袋里,拿上一柱香,把小炮插在雪地里点燃,“啪”的一声雪花四溅,红色的炮屑分布在炸开的雪洞边就像盛开的鲜花一样,要是旁边再围上几个小朋友,那是非常神气的。快吃早饭的时候,我们把院子里的雪铲完了,我嚷着要叔叔放炮,尽管小手和耳朵已经冻得生疼,尽管奶奶喊着让进屋暖和,我依然跺着脚催促着叔叔。无奈之下,叔叔说鞭炮咱不放了,给你放个“大炮”。尽管我不知道“大炮”长什么样子,好奇的我还是答应了。叔叔悄悄地在里屋的小箱子里取出两个“圆纸管”,然后各插上一段“炮线”,后埋在了大门外新堆起的雪堆里,叔叔像鬼子进村一般猫着腰将“炮线”点燃,在很响的“噗嗤”声中,叔叔拉着我躲到了院子最里端,并用力地捂住了我的耳朵,尽管如此,巨大的响声还是把我吓得大叫起来,以至于惊慌中将院角的铁炉也撞翻了。屋子里的奶奶慌乱地喊着:“咋了、咋了……”知道不妙的叔叔早已跑的不知踪影。奶奶拉着我的手,看着摔破角的铁炉,拍着大腿叫着:“坏了,坏了,你爷爷回来又要打你了……”我吓得哭了,不知啥时爷爷回来了,看着院子里的乱相,吼叫着让把叔叔找回来。那日,叔叔和我自然是少不了一顿挨打,我幸好有奶奶罩着,只是哭声大些,我不知道那是被吓的,还是打的……

后来,慢慢长大的我知道那次叔叔放的“大炮”叫雷管,就是工地上炸山用的那种,插的“炮线”叫导火索,都是叔叔在工地上干活时因为稀罕而偷着拿回家的。那个铁炉是爷爷托人在外地买的当时最高级最漂亮的铸铁炉,舍不得用,放在院角。难怪那次爷爷会发那么大的火,不过幸好那次的“大炮”没有惹下乱子,以至于每次过年放炮我都会想起这件事,也正是这样的经历,让我在多年的放炮中都格外的小心。
那时的冬天很冷,也许真的是穷,尽管冷的连手都掏不出来,城边塌底村的孩子们还要在上学时挎着一个箩筐,放了学再去机关单位烧过的煤堆里筛煤渣带回家继续用。爷爷不让我筛煤渣,也许是心疼我,也许是家里真的不需要。看着每天有同学挎着半框或一筐煤渣回家的得意样,我是无尽的羡慕。趁爷爷不在时刻,我偷偷的拿走了箩筐,在距家最近的邮电局的炉道里掏起了煤灰,倒入箩筐,一遍一遍地筛,一颗一颗的捡,我真的不知道这活居然是如此的不容易,那时的激情早已被满身的煤灰、冷汗和嘴唇上结冰的鼻涕所掩盖。终于搞出了半筐的煤渣,当我像一个“小土匪”似的出现在家里时,奶奶在一脸诧异的目光中笑的前仰后合,搞得我像个小丑似的站在那里不知所措,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筛煤渣的经历,现在的孩子自然很难理解这些。
那时的冬天很快乐。进入腊月,河里的水早已结了厚厚的冰,那时的屈产河水大且洁净,平整的冰面也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划冰车的、溜冰鞋的,什么也没有的就在冰面上“划远远”,还有年龄小一些的就站在河边看热闹,哪个摔倒了,哪几个撞在一起了,都会赢来一阵的狂笑,没有谁去考究那些可笑的成份。比较激烈的是划冰车比赛,整队出发,在激烈的呐喊声中,孩子们似牛犊般拼命划动着用钢筋做的“冰簪”,有的为了抢先,故意用冰车撞翻他人的冰车,往往都是大一点的欺负小的,愣的欺负善的,最后的赢家会得意地挥动着“冰簪”,就连走路的样子也和其他人不一样了。我因为瘦小,是从来不凑那个热闹的,即便如此,每次滑冰也都会将奶奶做的棉布鞋弄湿。后来,就是大家一起在河边架火烤鞋,烟灰夹着汗水把每个孩子都扮成了“花脸”,并相互取笑着,以至于让大家忘了吃饭,忘了寒冷,甚至忘了回家。也就是那年冬天,我的棉鞋被烤出了一个洞,奶奶在不停的埋怨声中,用同样的布给我又补了,那双带着补丁的棉鞋一直陪伴我到有了新鞋的一天。
那年冬天,我在雪地里数着脚印回家,转着圈儿回家。那时家中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我不想在奶奶的催促声中入睡,我知道,冬日我的快乐在外面,尽管天寒地冻,尽管大雪纷飞,尽管我只有一身已经泛白的黑棉袄、黑棉裤……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