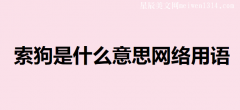当前位置: > 伤感文章 > > 正文
给您一个仪式,让我们就此道别
2018-12-25 23:13:57 作者:汝青
2008年深冬的一个上午,母亲执意要和我们一起到医院取前一天她的检查结果。在医院通往CT室的鹅卵石小路上,我回头看走在后面的母亲时,突然感到一向精神的母亲有些陌生:上身前倾,胳膊无力的垂落着,步履蹒跚,在瑟瑟寒风中,身体有些摇摆,一不留神好像就要倒下。
想起两个月前还在庆祝她,终于瘦了几斤实现了难买老来瘦时,瞬间有种莫名的惶恐。不及细想,我快步上前拉她坐到大厅一角的椅子上,去拿结果。医务人员将带我到一处房间,隐约中一丝不安掠过心头,他将结果给我时什么也没说,只是要了我的联系方式,我急速抽出单子跳过生涩的医学术语往下看,当看到“肺部阴影”、“转移”几个字时,脑子突然一片空白,许久蹲在了地上,我想让自己镇定些,可却止不住哽咽,望着远处孤独的蜷缩在墙角椅子上的母亲,久久不敢过去。
医生说手术已无意义,我们选择了瞒着她保守治疗,告诉她是一种严重的肺炎,必须住院治疗,她听说要住院,说:“枕头下放了五千元,拿来用了吧!少拖累孩子,用这五千尽量把病看了。”她不知道,不要说一个五千,哪怕十个五千、上百个五千,我们也想挽住她啊!
用了医生推荐的药,数次上北京找到在主流媒体做过专题报道的药,甚至用了据说能起死回生的含有从太空提取什么成分的药。可再传奇的药,在与癌细胞的较量中都败下阵来。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我来到凤凰山的弥陀村,上香跪拜许愿祈福……没有奢望,只想哪怕让母亲再留三五年。可她还是迅速地日渐艰难,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在疑惑地看过一次被换了标签的药瓶,想问什么被我们故作轻松的搪塞以后,她不再过问自己的病情,却一点点地安排了自己的一些事,于无声处,她让我们的回避不那么艰难。
母亲的呼吸日渐困难,在进一步检查后医生说:“用个不恰当的词形容你母亲现在的状态---苟延残喘。”在医生建议下,经过考虑,我们决定给呼吸已相当困难的母亲做支架手术。用支架打开气管,使她呼吸顺畅。可那是怎样的一个手术啊?应该是支气管镜下做的支架植入吧,极度痛苦的母亲强撑着配合医生艰难地进入一个支架,医生却发现比片子上看到的还要复杂,一个不行,必须再植入一个,我已经不敢看母亲了。手术做完后,她吐血不止,并且一股股浓痰不时就将气管堵严。她在我们一次次疾呼医生快来时,做了数番的挣扎。医生让我们做好准备,说还有可能瘤破裂引起大出血。我和姐姐、两个哥哥寸步不离守护着母亲,一直到黎明,情况依然没有好转,在医生的护送下我们将母亲转到另一家呼吸专科,三个昼夜,似乎是经历了三个世纪,情况有所好转,不再吐血,呼吸也开始平缓。那天,四十多岁的哥哥像个孩子一样说:“快看,咱妈笑了。”我们一看,母亲确实露出了那种经历生死磨难、以为闯过生死关头的艰难笑意,我却止不住的想流泪,急忙转过身去。后来,她基本不能下床了,进食越来越困难,却拒绝下食管。

她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了。那天晚上我陪她。半夜她咳了一阵,久卧在床,病魔带给她的种种折磨都藏在她的沉默里。我说:“妈,是不是很难受?我给你翻翻身捏捏背吧!”她摇摇头,然后张了一下嘴向外摆摆手,示意我去休息。我弯腰抱起了她,我能感觉到她还在奇怪不足五十公斤的小女儿是怎样将她抱了起来,而不知即将回归故里的她,身体已经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即便我们使出了浑身解数,三个月后到底还是要面对此生与母亲离别的无奈。
二零零九年九月的一个黄昏,妈妈走了。
从三十岁一直到患病卧床,她为村里服务了三十多年。村两委要给她开追悼会。她的悼词是我写的,那不是用手写的。那张被泪水浸透的悼词,是用心写得,直到今天,它仍在我心里。
妈妈,你厚道善良。作为村里那个年代唯一的助产妇,村上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经由你的手抱扶人间的。三四十年前的一个深夜,电闪雷鸣,暴雨滂沱,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有人要生产了,你应了一声立马起床。我说妈我跟你去,你说一会儿就回来了,孩子,你睡吧!然后拿把伞走了。这一会儿好长啊,天大亮了你才回来,身上的衣服还未干透。实话说我早就适应了这好长的一会儿和这湿漉漉的衣服,我不理解的是,这么辛苦的工作你分文不取还乐此不彼是怎么做到的。
妈妈,你慈爱贤良。我刚满一岁的孩子发高烧时,你匆匆赶过来,一个晚上一会儿一摸孩子额头,并不时还要为我拉上滑开的被子,你女儿和女儿的女儿一直都在你的呵护中。
妈妈,你习惯了隐忍不语,被我们逼到医院检查之前,您腹部已经数次剧痛难忍,你却一次次用手硬顶着不言声。你偷偷忍者,却不知这让我们以后想起了对妈妈的粗心都悔断了肠子……
我用了大篇的文字来写她,可女儿心中厚重的妈妈哪里是几个文字能说得完的。
无数次梦中,妈妈来了;无数次梦中,妈妈又走了。似来又去的梦境成了我挥之不去的痛。
妈妈,接受与你此生的离别,我用了好久。我终究是要让自己从你似来又去的梦境中走出来,因为,我应让爱女儿的妈妈心安才好!
既然时间没有冲淡记忆,那我就选择了这样一种形式让自己释怀——妈妈,给您一个仪式,让我们就此道别!
安好,母亲!
相关推荐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