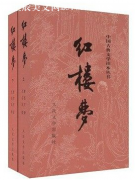当前位置: > 读后感 > > 正文
红楼梦读后感【8篇】
2020-03-22 23:39:09 作者: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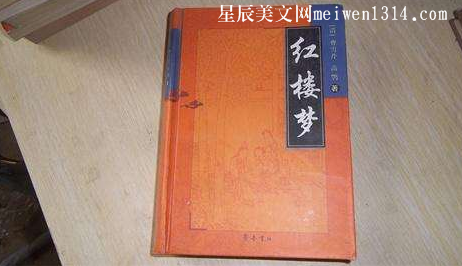
篇一:红楼梦读后感
作者:蒋灵妤
“边温言,边藏封喉丝千线。”
这是曹公笔触给我的感受,他清醒而委婉,浅淡又自然,他的笔下鲜有声嘶力竭,血溅三尺的场面,却总是以温柔刀割人性命。从没有人直白点明过贾府的衰败苍凉和灰暗凋零光景,只是第十二回秦可卿染病时是“百般请医疗治,诸如肉桂、附子、鳖甲、麦冬、玉竹等药,吃了有几十斤下去”,而七十回以后凤姐治病要人参,却只能“找出一些渣末”;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时凤姐随随便便就赏了她两百两银子一吊钱,可八十回后期王夫人要二百两银子都找不出来;四十回招待刘姥姥时“什锦攒心盒子”“围屏桌椅花灯”“四楞象牙镶金筷子”应有尽有,直耍的刘姥姥团团转,后来却是贾母吃的红米饭都不够……最终树倒猢狲散,各寻各自门之后也绝无死去活来的壮烈决绝,只是曲曲折折绕了一圈又回到开头的空空道人和僧人,甄士隐和贾雨村,荒唐言和笑其痴,在悲切的哭声里一梦到头,万境归空。或许世人见惯了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惨烈收场,他偏要用华丽的衣裙与令人惊艳的好颜色来描述死亡。
贾宝玉梦中呐喊不认的金玉良缘,最终却是举案齐眉,落得个美中不足,到底意难平;两情相悦的木石前盟,却是认错了人,报错了恩,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上演情深不寿,天不假年的戏码;元迎探惜四春一个恨无常,一个喜冤家成了风前薄柳一个分骨肉,一个虚花悟看破浮华遁入空门;聪明泼辣一世的王熙凤却是机关算尽误了性命,一张草席魂归金陵;更不用提那有命无运的英莲,有运无命的可卿……人世间的遗憾和无常简直要顺着纸浆淌下来。
可这些苍凉有天命难违也有人事所致。
曹公笔下不少那些乍见淡淡而过,到后头回想却忍不住心惊的因果机缘。看黛玉湘云的中秋联诗由“三五中秋夕,清游拟上元”的欢愉到悲愁寂寥的“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再到后来妙玉续上的十三韵,一句“钟鸣栊翠寺,鸡唱稻香村”暗示了贾府由盛转衰的悲凉结局;看秦可卿死时给凤姐托的梦“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的谶语,之后迎春出嫁死亡、探春远嫁、惜春出家之后贾府的渐渐不济……一切都在安排。而贾氏祠堂里那声散在风里的喟叹,也终究是拂过了人们一步一步种下的因,为它们的果更添一份必然了。不知黛玉曾说过的死生有命和那句“入不敷出,长久下来不知如何是好”的忧虑,是不是隐隐参悟了天理昭彰,终有轮回,福祸相依,否极泰来的道理?
合上书页,眼圈微红,香腮带赤的红楼女儿们入我梦来也仍旧颦笑顾盼,可那厅堂外总是天降大雨竟夜不歇,我想着那些欢愉终究是泛黄一场故梦,而纵然是分别是我行迟迟,那群芳争艳的春天,终究是凋谢了。
篇二:红楼梦读后感
作者:吴政泽
《红楼梦》一部书流芳百世,故而引申出了许多令红学家们世代研读探究的红学分支,考证、索引、批注、释义,错综复杂,层出不穷。然而艺术生于创造的想象,不必实有其事,不必一定与作者的身世相照应,更不必字字句句皆有引典、双关——我们读红楼梦,还是应当回归文本,在曹公的字里行间读懂每位人物的形象特点。
林黛玉作为书中的主要人物,历来受到褒贬不一。很多人都认为黛玉初进荣国府一段是最能表现其人物性格的,但在我看来,林黛玉最生动形象的体现是在第二十至四十回,也就是曹雪芹着力描写宝黛钗以及姐妹丫鬟在大观园中的风花雪月之时。黛玉情感上是多愁善感的,宝玉不经意间的一个玩笑、一个动作、一句言语,都常常使得她夜不能寐、暗自思酌;她在性格上是率真大胆的,她没有像恪守妇道的李纨一样,表现得温柔贤惠、举止得体,她与宝玉共读《西厢记》,常常与丫鬟姑娘们说笑,丝毫没有小姐的架势。
黛玉的性格决定了她对于人生的看法,她既不追求团圆热闹,也不要求自己的爱人走上仕途道路。她其实一生中仅仅有两样追求:一个是生活情趣,一个是知心朋友。比如第二十三回,宝玉问她“你住那一处好?”林黛玉笑道:“我心里想着潇湘馆好,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梨花芭蕉、粉垣翠竹,无一不被黛玉写进自己的诗歌,产生对于景色的共鸣。
而黛玉能与紫鹃交心,情同姐妹,愿意教香菱学诗,这表明黛玉心中对阶级观念与宝玉相似,较为淡薄,而对人情世故、是非曲直更为在意,初相识大都会认为宝钗更易相处,但相处久了却能与黛玉交心,从湘云对钗黛的相处就可证明这一点。
黛玉和宝玉的爱情是悲剧的,但又不完全是悲剧的,只是带上了悲剧的色彩。红楼梦中不止一次对于宝黛爱情的形容是用一个“痴”字的。但这种爱情的“痴”也同样体现了他们之间感情的纯粹——情不知何起,一往而深也。用朱光潜的话来说就是:“美感的态度不带有意志,所以不带有占有欲。”黛玉和宝玉两人对有爱情都不拥有丝毫的占有欲,于是都把对方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揣摩、去欣赏。
“不想日未落时天就变了,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四十五回中的这个场景,与那些浓郁的感情、冲突强烈的戏剧相比,这个夜晚发生在潇湘馆里的事情,实在太过平淡而琐碎。但也就是在这个夜晚,黛玉第一次向宝钗倾诉了寄人篱下的苦衷。黛玉对于宝钗情感的变化,也是《红楼梦》中体现人物关系的一条主线。脂批云(庚辰第四十二回“回前评”):“钗,玉名虽两个,人却一身,此幻笔也。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故写是回,使二人合而为一。请看黛玉逝后宝钗之文字,可知余言不谬矣。”至于钗黛是否真的能够合一,至今无法定论,但是这样一个善解人意、通情达理的黛玉,又怎么是目下无尘、爱使小性呢?
五柳先生在傲霜残枝中见出孤臣的劲节,和靖先生于暗香疏影中见出隐者的高标,两人一位爱菊、一位爱梅。而林黛玉对于海棠的热爱,也不逊于此二人。她在《葬花吟》《秋窗风雨夕》等诗词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忧愁、憔悴、柔婉形象,甚至于她的悲剧遭遇,都与李清照颇有几分相似。看完《红楼梦》,再去回看易安居士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一句,未免不联想到潇湘馆里临窗而卧、嗔怪紫鹃的颦儿啊。
至于林黛玉的结局,众说纷纷,各有各的道理。除了高鹗续书中其“焚帕而亡”“泪尽而亡”的情节,还有刘心武根据判词“玉带林中挂”提出的竹林中上吊自缢而亡的推测,等等。在我看来,还有一种可能是她如葬花一般随流水而去,即饮恨投水而亡。如果怀揣这样的想法重读《红楼梦》,其实会发现有很多依据是可以支持这个假设的。其中最明显的是黛玉总是将自己比作西施,言行举止容貌,尽得西施颦眉之风流。而西施就是投江而去世的。
还有一种推测是死而复生。红楼梦里在影射林黛玉命运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荆钗记》、《钗钏记》、《牡丹亭》这三部剧,这三部剧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女主角死而复生了,这绝非巧合,似乎强烈暗示红楼梦剧情的发展——女主角林黛玉也可能死而复生。在《荆钗记》与《钗钏记》这两部剧里,女主角钱玉莲与史碧桃都不约而同地投水自尽了,但又幸运获救。但是里面的男主角王十朋与皇甫吟当时都误以为爱人已死而悲痛不已。这样类似的桥段,恐怕红楼梦也会有。
但终究,这些仅仅是推测罢了。就如张爱玲所说:“人生有三大憾事,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当年的那些春风拂竹、笑颜嬉雀,终不过鹅幻一场,难免落得“花落人亡两不知”。
唯有颦卿,那痴嗔娇怨、题帕舞袖的依恋,那才华横溢、冰清玉洁的性情,和那无依无靠,红消香断的惆怅,在葬花一吟、仰天长问的一刹那,得以亘古回响。
湘帘倚恨,人去也,潇湘馆外,海棠凋落,却见鹦鹉,尤啼如故。
篇三:红楼梦读后感
作者:曹铭轩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简单二十字,便道尽整篇小说,之所以被列为《四大名著》,《红楼梦》的确有其匠心之处。
书中的金陵十二钗,可谓各有千秋,但薛宝钗和林黛玉并列首位,又都和宝玉有着爱情纠葛,故常常为人所比较。以我所见,她们之间,同而不同。
首先,她们出身不同。林黛玉出身书香门第,而薛宝钗则为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单就高低,宝钗略胜于黛玉,环境也造就了两人不同的志趣。黛玉可谓是才女,孤高清傲,对功名利禄毫不在意,而宝钗则是知书达理,和当时的世人想法一样,希望宝玉努力修学,考取功名。想法本无对错,只是一人叛逆,另一人传统而已。
其次,她们的性格迥异,书中时常有黛玉“半含酸”,却鲜见宝钗哭哭啼啼,黛玉的心思很细腻,多愁善感,父母双亡后寄人篱下,令她更添几分孤寂,由此,她与姐妹们相处,总是有些不自在,有过和湘云的口角之争,有过和宝玉的怄气,有过与宝钗的斗心眼儿,她的强烈的自尊心,表现出来的是尖刻的话语,但其也不是为讽刺而讽刺,更多的,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罢了。当然,就如青白眼的阮籍,对待常人态度不冷不热,但是遇到厌恶的,如告密的赵姨娘,就根本不拿正眼瞧她,其品性之清高可见一斑,可也有例外,和自己志趣相投的,如妙玉,则恭恭敬敬,少有地称赞他人。再看宝钗,温婉近人,毫不夸张的说,宝钗就是封建妇女中的德才兼备的典范,她或许不如黛玉有才,但是为人处世,却比她老练稳重。自小接受着良好的教育,她恪守礼法,不离经叛道,做事合乎理,当然,无人生来如此,虽出自皇商薛家,但是家族延续早已日薄西山,父亲早逝,哥哥不肖,她需要承担起家业的重担,过早地懂得人情世故,这也是她的不幸之处。
最重要之处,就是两人对宝玉的感情。宝玉和宝钗的爱情是“金玉良缘”,和黛玉的爱情,是“木石前盟”,宝玉和黛玉是青梅竹马,自黛玉进了贾府,如同淤泥中的莲花,为社会所不容,唯一让她宽慰的,就是宝玉对她的那份真挚而又纯洁的感情,也正因为这份羁绊,使得她对两人的关系特别敏感,当宝钗一进大观园就深得少女喜爱,但当时贾府不过是她的暂歇之处,无意与宝玉有什么瓜葛,但是黛玉的过分敏感使得她起初对宝钗心生间隙,但是自两人逐渐了解了对方,我认为与之叫做宝黛之争,不如说是彼此互补,以对方之长去慰自身之缺。宝玉的心,自始至终都是系于黛玉身上,但是贾府的限制,使得这段感情必然会破灭,唯一牵挂的事物的消逝,也致使了黛玉之死,宝钗不是罪魁祸首,换做他人,这段爱情依然不会长久,只能说是贾府和社会逼死了黛玉。而宝玉虽然对宝钗功利的看法不满,但却不讨厌她,三人的关系很微妙,彼此之间总有争吵和不满,但是却互不可缺,毕竟彼此之间都是知心好友,黛玉的才情无人能及,《葬花吟》乃传世之作,但是宝钗对世间的认识也远胜他人。两人在对宝玉的感情上都是被动一方,黛玉是因为其孤高的性格,使得她的内心向往,却怕自己失去,只好表现出冷傲的样子,偶尔和宝玉独处时才会展露出真我,宝钗内心想要接近,但是明白宝玉心中只有黛玉,加之她所受的教养让她不能为自己的人生大事做主,故体现出尴尬的处境,但有时,真实的情感让她不由得羡慕两人感情,那些调笑中,带有的是辛酸和悲伤。宝钗虽然和宝玉喜结连理,可这应该说是三人悲惨的命运结局,三人再难聚首,黛玉香消玉殒,宝玉违心地被迫选了“金玉良缘”,宝钗只能接受痴痴呆呆的宝玉,随着情节的发展,他们的命运,奏响了一曲悲歌。
读罢全书,方知曹雪芹的悲哀。在封建时代,她们生来就受到命运的羁绊,想要挣脱,却无力反抗身上的枷锁,遁入空门,远离世俗,已经是最好的归宿。恰似路易十六,他没有做错什么,但是身份昭示了他的结局。红颜薄命,这是她们的悲哀,也是曹雪芹的悲哀,更是时代的悲哀。林黛玉好似精灵落入凡尘,宝钗则是人间极致,一个代表反对,一个代表接受;一个代表孤傲,一个代表温和;一个代表情深意浓,一个代表默默守候。没有所谓的谁高谁低,迥然不同的人生,最后都是殊途同归。
篇四:红楼梦读后感
作者:盛杨
要评说《红楼梦》中的人物,首要的当数男主人公贾宝玉了,作为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作者曹雪芹在其身上着力最多,寄托也最深,他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甚至人人还说这一形象所影射的就是曹雪芹本人。
但据我看来,这一典型形象绝非作者的实灵自作,而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中同类型的人物加以概括,并揉合了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完美艺术形象。
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有两首《西江月》。
初读这两首《西江月》后,就此认定了宝玉是一个不求上进,只爱脂粉的孽根祸胎。但其实不然,这两首《西江月》是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出发,所反映的是封建大家长对宝玉盼着他中举,扬名以继承地主阶级事业的“良苦用心”。而作者正是借《西江月》寓褒于贬,充分概括了在宝玉身上最突出的闪亮点---叛逆性格。
词中说他:“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其实就是说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愿走封建家长为他规定的读书应举,结交官场,遵从礼法,经帮济世的人生道路,而是鄙视功名利禄,厌闻“仕途经济”的学问。他甚至认为那些和朱理学之类的儒家著述,“都是前人无故生事”是“杜撰”出来的。至于八股时文更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拿安诓功名混饭吃的”。他把封建统治者奉若神明的儒家道学批评的一文不值。基于此种想法,他“杂学帝搜”,宁肯去读《西厢记》《杜丹亭》这类被封建卫道者视为邪书的“小说淫词”,也不去读《四书》、讲八股、听“仕途经济”的“混帐话”。
他对读书上进、为官做宦的世俗男子,有着强烈的憎恶和轻蔑。
不仅如此,在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中,史湘云劝他:“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宝玉听了十分逆耳,忙说:“姑娘请别的妹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
贾玉玉的叛逆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坚决不肯走封建主义人生道路,还表现在他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大胆地提出了挑战。当然,在他的性格当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也就是对于世俗男性的憎恶轻蔑以及与之相反的对于女孩子的特殊亲爱和尊重。在第二回中,他发表了自己离经逆道的独到见解:“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为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后来随着宝玉逐渐长大,他的思想也日趋成熟,他又发现“女儿”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又有女儿由出嫁前的“无价宝珠”到出嫁以后变成“死珠”再最后竟变成“鱼眼睛”的看法。这表明,他在成和或逐渐认识到在封建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就是女孩。因此,他在行动上才表现出了对女儿不同一般的温柔体贴。
还有,就连宝玉追求的爱情婚姻也是建立在这种反叛思想的基础上的。他早已将追求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昭然明世,他在梦中叫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甚至拉着袭人的手把对黛玉的满腔情都倾诉了出来。
因此,也有人说贾宝玉这个形象所体现的是初步民主平等思想。但毕竟,他的思想还是有一点狭碍的。例如,他不敢与封建制度彻底的决裂;他从来不敢和封建家长正面发生冲突,对抗比较消极;还有当他苦于找不到思想出路时,就产生了想死,想“化烟化灰”的虚无空幻的思想。
篇五:红楼梦读后感
作者:赵乐怡
史湘云是我读完本书之后颇为喜欢的一号人物,甚至多过对其他主角的喜爱。在曹公的笔下,湘云是一位具有中性美的女子形象。她心直口快,大方豪爽,不拘小节,爱着男装,同时却也有诗思敏锐,才情超逸,说话“咬舌”,把“二哥哥”叫作“爱哥哥”。她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令人喜爱、富有“真、善、美”的豪放女子。
我很喜欢周汝昌《红楼小讲》中对湘云的评价:
“海棠和菊二花,是湘云在书中的象征,棠喻其才质之美,菊喻其品格之高。海棠无论春秋,花最芳艳可爱,而菊则傲霜冒冷而开,丰神骨气,迥异凡花。在一层意义就是至秋百花早尽,菊实为花事的终结者——在全书中独她旧存而不似诸女儿的早殁先调。”
而在《红楼梦》的记载中,第十八回,贾宝玉《怡红快绿》一诗中有句“红妆夜未眠”也是把海棠比喻为睡美人,在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卧芍药裀》中有一番精彩的描述:
“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嚷嚷地围着她,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药花瓣枕着。众人看了,又是爱,又是笑,忙上来推唤挽扶。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唧唧嘟嘟说:‘泉香而酒冽,玉盏盛来琥珀光,直饮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却为宜会亲友。’湘云慢启秋波,见了众人,低头看了一看自己,方知是醉了。”
表面写的是芍药,实即是指“海棠春睡”。因而在第六十三回,湘云抽到的又是一根海棠签,题着“香梦沉酣”,诗云“只恐夜深花睡去”,黛玉即笑道:“夜深”两个字,改为“石凉”两个字,意指湘云酒后卧石的轶事,实即说明了作者是把湘云指喻为海棠的。
在大观园中,史湘云的身世既富且贵,虽因家道中落、不复为富,却也不端着贵族的空架子。她既无视高低贵贱,又不拘于男女之别、与人相交、一片本色、无功利之心。这也与她的身世有关,湘云从小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她的婶母待她并不好。因此,她的身世和林黛玉有点相似。但她心直口快,开朗豪爽,淘气,又不大瞻前顾后。她敢于喝醉酒后躺在园子里的青石板凳上睡大觉;和宝玉也算是好友,在一起有时亲热,有时也会恼火,但毕竟胸襟坦荡,“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不过,另一方面,她也没有林黛玉那种叛逆精神,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薛宝钗的影响。在史湘云身上,除她特有的个性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封建时代被赞扬的某些文人的豪放不羁的特点。比如在凤姐调侃龄官长得像一人,唯有湘云心直口快地说出像黛玉,最后也引发了一场宝黛之间的争执。
篇六:红楼梦读后感
作者:杨如沁
红楼梦中有十二位最为优秀的女儿,被人们合称“金陵十二钗”。而在这十二位女性中,几乎都与“贾王史薛”四大家族有血亲关系,但是在之中有一位女性游离在四大家族以外--妙玉。
“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妙玉作为金陵十二钗之一,与四大家族的关系也仅仅是借住在贾府檐下,出场的次数与给人留下深刻记忆的名场景并不多,相比“黛玉葬花”“宝钗扑蝶”等脍炙人口的女性角色性格突出的名场景。在妙玉为数不多的登场中“妙玉斟茶”便是了解妙玉的一大窗口。妙玉自小因体弱多病,而入了空门,出家后带发修行,师父去世后入贾府,入住栊翠庵。妙玉一生修行,在佛院庵堂度过,却没能收起自己的尘心,与邢岫烟交友至深,对贾宝玉暗含情意。
在刘姥姥二进荣国府时,贾母两宴大观园,带了众女儿到栊翠庵品茶。妙玉盛情款待,茶具、茶品、选水皆体贴各人心意,另请了宝钗、黛玉去耳房里吃梅花雪茶。宝玉不请自来,妙玉用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给他斟茶,接着寻出一只竹根大盏斟与他,取笑他“饮驴”,又嘱咐道:“独你来了,我是不给你吃的。”黛玉问水,被妙玉取笑“大俗人”。刘姥姥吃过的那只成窑杯,妙玉嫌脏不要了,宝玉便说情送给刘姥姥。
从这时便已发现妙玉作为佛家子弟却对俗世情爱的一丝依恋,而到了宝玉观妙玉惜春下棋时,妙玉心动面赤,彻底跌入俗世凡尘,而后患梦魇,预言了自己遭劫遇害的结局。
作者借妙玉一角色表现出一位茶道高人应有的茶礼仪修养。她与贾母问答之间,含有“斗茶”比拼之意:一斗茶品,贾母出题说不吃六安茶,妙玉预先献上了老君眉;二斗选水,贾母出题问是什么水,妙玉预先选了旧年蠲的雨水。这两个回合,妙玉都想在贾母前头,可以说是在红楼梦中的茶文化代表人。
除茶文化外,妙玉身上的另一个标签--悲剧色彩也是曹雪芹塑造该角色的一大中心。妙玉重视自我心性修养,却过了火,明明忘不了贾宝玉,但又塑造出自己心性高洁,故而常怀“花因喜洁难寻偶”、“一生傲岸苦不谐”之慨,在人世间淡泊名利,曲高和寡的形象,因而妙玉在红学中所得到的评价多数为“故作清高”“令人生厌”“嫌贫爱富、趋炎附势”的骂名。但是比起批判角色本身,我们更应该看到作者想通过这一角色传达出的社会信号,妙玉心性高洁,一生傲岸,贵为“金玉质”,到头来却被贼寇劫去下海,陷在最肮脏污秽的泥淖中,惨遭迫害玷污,命运最为悲惨,她的悲剧寄托了作者对不合理的末世社会现实的一腔愤懑。
金陵十二钗里其他的女性虽然都有着悲剧性的命运,但是比起她们,在妙玉的身上更能看到美是怎样被摧毁的。
篇七:红楼梦读后感
作者:余佳凝
判词云: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
曹公塑造的晴雯的形象深入人心,一个面容姣好,心灵手巧的丫鬟,在宝玉手下使唤。她天真、直率,但奴隶出身的她,与贾府(清朝的封建制度在书中的映射)的风俗不洽,终难逃冤死的命运。她是宝玉和曹雪芹梦中的芙蓉花仙,是清朝人们心中理想的女子,拥有超越时代的想法。
心比天高
晴雯撕扇一事中,因跌折了宝玉的扇子,宝玉训斥了她几句,晴雯的自尊心便受到伤害。最后还是宝玉惯她听她撕扇,才了了事。从这事儿不免体现晴雯的天真,为其后来的遭遇埋下伏笔。但能看出她追求平等,勇于反抗,拥有与那个封建的时代不协调的精神。她孤傲不逊,锋芒毕露。
身为下贱
相比袭人拥有完整的封建小家庭,这个家庭给她传统观念和价值观的形成塑造提供了环境。晴雯身世不明,被贾府家的奴仆买来,成为奴隶的奴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泥沼之中,受苦受难且长期不受重视的生活正是她极强自尊心的来源。贾母也喜欢她,说言谈针线,丫头们都不及她,将来还可以给宝玉使唤的。
风流灵巧招人怨
这又不得不提起晴雯补裘的故事了。宝玉赴舅舅寿宴上穿的俄罗斯雀金裘不防后襟子上烧了指顶大的小眼,因天晚找不到懂行的裁缝,晴雯顾不上病,叫人找来孔雀金线,亲自动手一针一线织补,直至天快亮时才补好了。
晴雯与黛玉一样,用情做事都是随心的。然而,心灵手巧的她却不屑于以自己的“风流灵巧”去博取封建统治阶级的赞许。她懒,并不是因为她不想做,而是因为她不愿以一个奴隶的身份去做。她只是希望站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以一个人的身份,为着自己的心而做,她爱宝玉,才病补雀金裘。
寿夭多因诽谤生
晴雯入贾府以来,由于直率的性格,得罪了不少等级与地位比她高的人。当然也有不少嫉妒她的颜貌和手艺的。晴雯的香消玉殒大多是因为招到他人的诽谤引起的。贾母也有言,谁知(晴雯)变了。
多情公子空牵念
晴雯死前,将左手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铰下,给宝玉珍藏。晴雯是黛玉的影子,她的个性与黛玉相似,宝玉是像黛玉一样待她的,他在太虚幻境梦见过她,可怜姑娘的悲剧人生。
她是金陵十二钗又副册之首晴雯,她是生错时代的姑娘晴雯。
篇八:红楼梦读后感
作者:徐睿婷
《红楼梦》中,贾母作为一个家族的管理者、智慧的生活家,她身上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我。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够格的贵族。
书中四大家族都是名门望族,但是有贾母这样气质的却少之又少。宝玉、宝钗、黛玉等人因为太过年轻,注重的大多是诗词歌赋、风花雪月;凤姐虽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方法,但一贯的严刑峻法使她过于强硬,另一些名门子弟,如贾赦、贾政之类,都有自身性格、行为上的缺陷,无法跻身贵族一列。
首先,从根本上说,贾母有足够高的政治地位。五十八回宫里的老太妃薨了,有爵位之家要入朝随祭,安排下处时,下处是一个大官的家庙,中有东西两院。古人以东为尊,即便北静王府毕竟在政治地位上高于公府,王府却主动居于下首,赁了西院。这点可见贾母的地位。在“清虚观打醮”一回中,贾母一人坐八人大轿,也证明其身份高贵。
其次,她有着贵族的气度与作为一位老人的温暖。还是“清虚观打醮”一回,小道士不小心撞着了凤姐,凤姐二话不说就打,十分张扬,也有些惹人生厌。而贾母劝着要好好对待小道士,念在他年幼,给他钱买果子。这里可以看到她心中的大度与柔软。贾母也是为数不多看到刘姥姥身上智慧的人,比起其他人的嘲笑与嫌恶,贾母更聪明,更懂得体谅。一个真正的贵族,不应该视人命为草芥,而是要有像贾母一样的闺秀风范。
但是,贾母作为掌权之人,她讲究门面规矩,也有严厉的一面。袭人的母亲死了,袭人没有参加聚会,她却没有宽容她,说做奴才的讲不起这个理,即使有孝在身,主子也是主子,得过来伺候。贾母的两面交织在一起,反正是有软有硬,足够贵族范。
作为大家闺秀,她有很高的美学修养,对饮食、艺术等有着独特的认识,同时喜欢热闹、有童心,能和年轻人玩到一块儿。她不守着世人所想的老太太的样子去过安稳日子,而是从未放弃自己的喜好,赏花弄月、懂茶更懂音乐,让自己的生活过的多彩、有趣。比起同样出身高贵的王夫人,贾母更有灵性,更有趣。
很多人说贾母偏爱。其实贾母只是喜欢生的清秀的孩子,才会偏心黛玉等人,而贾母疼宝玉,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宝玉有她丈夫的影子,看着这个孩子,回想起了之前的日子。一位老妇人,对子辈孙辈有偏爱也正常,没必要过于计较。但其实贾母偏向了二房,也是家族内部不和谐的其中一个原因罢了。
因为贾母具有上述难得的品质,使她在贾府拥有极高的威望,这些是财富所换不来的。而且,贾府之所以能够形成自宁荣二公以来皆宽柔以待下人的风气,也跟贾母大有关系。贾母的身上有着很多在当时难能可贵的品质,在一些决策点上面都能够给予很准确有用的指示,她也是我在书中颇为敬服的一位人物。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