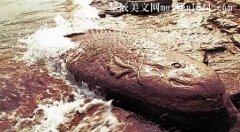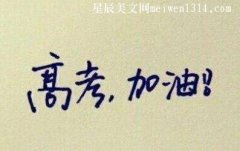说不尽的那时候
2017-08-17 23:12:44 作者:张晓琴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
照片上,刘海被春风撩得老高,红扑扑的脸颊,一件大红呢上装,与背后的金黄形成的番茄炒饭式的搭配,在当时很大胆抢眼,到现在我还觉得挺时尚前卫呢!这一晃竟快三十年了!
那时候,我和现在一样穿衣大胆。
粉红色的超短西装、背心、套裙,自己设计,和裁缝师傅边商量边缝制。农村师傅当时还不懂西装的裁剪方法,很积极地买书自学,最终成衣我很满意她也很自豪,觉得做出来的有大上海的范儿。
那时候农村学校同事大多是民办教师,年长头发花白的居多,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总是爱怜地把我的上装使劲往下拽:“丫头,是不是布料不够啊?你也可以凑件长的,不要做短的就够了!……”
那时候,学校很小,天地很大。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不是个呆子也是个疯子。一周二十多节课,涵盖所有学科,语数无外,音体美自然(现在叫科学),哼哼,还兼校运动队教练、广播操教练、校合唱队领队……居然还跨界去别的学校兼职训练合唱!
不是我全能,是一旦任务来了,全校最多九个人就我一个年轻,其他最年轻的也四十多头发全白。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丫头啊,你科班出身,我们负责后勤打下手!”
我硬着头皮上,也混到了几个奖,什么美术参加市里的比赛,合唱队、运动队、广播操在乡里拿个第一,把我这个在毕业前一开口同学们都笑瘫倒地上的跑调高手,变成了跟着风琴能哼哼的唱歌老师(那时候不叫音乐)。用现在的话说“拿奖拿得手发酸”,可惜了,是杂牌的大杂烩。
不过,没有那时候的杂七杂八,也没有现在的得心应手。那时候,本来一周只有周日一天休息,为了大家叫我的声“丫头啊”,我一年到头的休息都取消了,周日也上课。日复一日,从晨曦初露到夜幕降临,乐此不疲。
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可是很快乐。

带着孩子们种黄豆烧野炊,操场上贴烧饼打号子,大个男生打着领带死死地顶着喉结、穿着所谓的西装走哪儿跟哪儿就是保镖,那是不能让我有丁点儿闪失的架势。(星辰美文网www.meiwen1314.com)
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和孩子们用铁锅支起来爆炒肉片,吃得满嘴泛油,腮帮乌黑,路过的乡亲也狂笑不已,至今仍像油画样定格成了永恒……
那时候,乡亲很纯朴,气氛很融洽。
不足十平米的办公室里放扩音器的地方就成了灶台,电饭锅里青菜糊糊面冒着热气,男同事们弄点儿小酒就着猪头肉,咂咂嘴,红着脸,有一句没一句的山海经,时而狂笑,时而为谁要多喝一口脖子青筋爆出,一顿饭下来,大汗淋漓。室内的骄阳酷热与室外的皑皑白雪便是冰火两重天的和谐。
下午,吃剩的油饼可以做教具:“同学们请看,一个油饼是单位1,你和同桌平均分一人就是一半,你的一半用分数表示是什么?说对了油饼给你吃。”
那时候,人称“下茅坑”的那个孩子坐在我的自行车后座上复学;那时候,那个叫“龙”的孩子天天护送我下晚班;那时候,村玩具工厂的师傅天天送开水给护校的我;那时候,学校邻居大妈将鸡蛋卧在玉米糁粥里送过来给我当早饭……
那些只属于那时候的春夏秋冬已消失在逝去的青春里,也成了我这时候永葆青春的源泉。
猜你喜欢
热门推荐